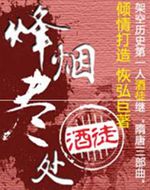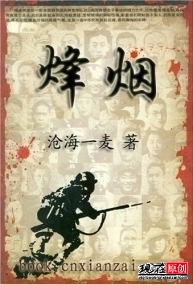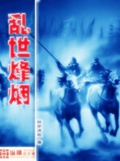烽烟杂感随笔集--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夜晚又一次摔倒,
化作文化的一道黑幕——
烽烟自选诗《盗墓者》
(一)
文化的价值意义有一半掌握在活着的人手中,而另一半则掌握在沉埋的死者手中。通过科学技术的整理,复活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并构建文化谱系,这是考古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存在的重要原因。为历史接骨,完成文化显露中文明的复活。
“我感到我爱上了吾珥,它那晚霞中的美景,热格拉堤挺然屹立而又朦胧模糊,浩瀚的沙海被映染成绚丽的黄、白、蓝、紫和玫瑰色彩,无时无刻变幻莫测。我喜爱工人们、领班人和提着小蓝的男孩们,发掘就是男人们全部工作和生活。不断涌现的历史的魅力紧紧抓住了我们的心灵。当眼看着一把短剑慢慢被刨出来,它携带着金色闪光,浪漫传奇也随之在这些砂、土中出现了。从砂、土中小心翼翼地捧起锅罐和其他文物,也促使我热切渴望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吾珥王陵发现者伦纳德·伍利)
在这段沁人肺腑的文字里,英国的考古学家伍利向我们欣喜地描述了吾珥王陵发掘的事件。历史的魅力此刻显现出无比诗意,这柄泛着金色光芒的短剑,就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萨默瑞恩人的文化。一段不朽的文化。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虔诚心理下的合法的发掘行为轻轻开启了文化之门。
而这,是文化的福音。
(二)
黑格尔把人类的自由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外在的控制下得到解放,二是从内在的情欲束缚中得到解放。外在的通过征服自然来得以体现,内在的通过情欲和物欲的调理来摆脱。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进程其实就是先“破”而后“生”的过程,这种行为目前已得到人类广泛的趋向于美好的认同。但人类内在情欲与物欲的扩张,却朝着另一种广义上的“恶”的方向前进。世俗化的获取,不但将以政治与战争来实现,同时,其精神指向将以文化的牺牲作为高昂的代价。文化的一部分在硝烟中沉埋大地,由于沉埋的这一半能产生直接的历史考量价值和艺术再现价值,在追求文化还原世俗物欲的前提下,文化在墓穴中的呻吟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盗墓者”的私欲。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带有明显地域性和地方文化色彩投影的坟墓,因其人类精神根源中对生死保持平衡感的渴望,因而坟墓无论是从造形上还是内部精神寄予上都作了区隔。这种区隔,既是生与死的区隔,也是文化的区隔。所以,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这种约束,在当时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文化的意识的维护上来,仅仅是宗族式的精神上的简单维护,这使坟墓在埋下珍宝的同时,也埋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灾难。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宋代以来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铁围山丛谈》载,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在回顾盗墓与文化发现的历史时应当指出,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和行为习惯之粗莽,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遭损毁,使历史文化信息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
这是文化盗墓者的初级体现。这种表现使反盗之术诞生。如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反盗墓的形式中,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以据说曾经“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的曹操所设置的“疑冢”最为著名。民间传说曹操有“疑冢”多至72处。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写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王子今《文化视野中的盗墓史》)
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文化知识及信息的“伪掌控”反过来对文化施以行盗者,试图借此达到个人私欲和权力的真实拥握。此类人谓之“高级文化盗墓者。”这就使“盗”与“道”因某种机缘而巧合一起。一方面,当孟子把公孙衍、张仪之类无原则的谋略家称之为“行妾妇之道”,当公元前218年97岁的荀子为自己过去不肖的弟子李斯相秦而愤然不食的时候,他们是在维护正义,用简单的行为捍卫“道”的纯粹性。但他们绝没想到这种“道”将成为“盗”的利用者和同化者。他们以及继承者,在痛斥文化盗墓者的同时,领悟到“道”之于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有针对性地制定“术”,因为痛斥与绝食已经扼制不了文化盗墓者的强悍理性。另一方面,“盗之术”与“道之术”的相互纠缠,使“盗”与“道”同时被谋略化。遗憾的是,很多情况下,“道之术”却变成了谋利的手段或工具,从而失去对“道”的终极诚信。
(四)
一晃几千年过去了。
在中国大地上高达22000个墓室被非法闯入的过程中,相信敦煌破旧的马车是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马车,而世界列豪的博物馆陈列着的发光的中国文化史,每一张扉页隐忍着屈辱。
文明的消隐,使人性的另一极端裸露,不管是对文化艺术信息墓府的盗掘,还是对文化学术思想上的盗取,都是对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的践踏。从这个角度讲,一部中国文明的历史就是一段文化盗墓者不断践踏的历史。虽然有“道之术”勉力发出哀婉的声音,但在日益世俗化的强大的物欲面前,一切弱不禁风。
而道德漏下的光明,终究未能覆盖大面积沉沦的人性。虽然文化价值的火种仍在民间。
2004/9/27于深圳
第四篇:文化的“借尸还魂”
第四篇:文化的“借尸还魂”
技术创作的“借尸还魂”与文化中介机构存在拷量
文/烽烟
文化的脚步,离开“大漠文海”,
来到“诗意”栖居的“水云烟坊”。
它注定是人类公有的“心灵家园”,
而非一位独领风骚的“单纯女人”——
烽烟《文化的脚步》
创作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可能感知到的各种秘密变成一种类似社会公约的文本存在,并昭示给公众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人类秘密的裸露及社会活动的审视随着挖掘数量的增加,文本将出现如“道德失落”、“身体回归”、“社会边缘化”、“文本意义虚无”等怪异现象。这时候,艺术创作就必然通过“策略”进行空围。
而“借尸还魂”的技术,成为文本创作的常用手法。
“借尸还魂”的核心是指:通过对“死亡物象”的有效鞭笞让其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其过去存在的价值意义。如我们把“大海”比作“母亲”,就是让“大海”失去自我后(“死亡”),通过审美喻意转化为另一物象指征“母亲”,然后以新的形象魂归故里,形成价值互动或转化。
从中国传统美学上说,艺术创造的极高境界常常就是一种“自然”,而非现在所说的“陌生化”创作观。中国传统文化天马行空般的形态表面看一直远离各种生活束缚和文本公约所带来的循规蹈矩,而其实质仍然是技术与经验、思想与存在的浪漫搭配。假如说文化的熏陶和濡染也能形成技术的艺术化,那么石涛的狂言一语中的:“至人无法”(请注意:不管是无法还是有法,都是技术,这是文本存在的首要条件)。高明的艺术家是“无法可依”的,就像康德所言,天才是给艺术制定规则的人。如果我们从儒家的大道回到道家的羊肠小道来看,创作这个问题将更加玄妙:天才不过是“道法自然”(老子)而已。细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所谓艺术家的天赋也就是那种“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状态,是“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让技术形成了锁链,或者说让技术达到最高形态,所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庖丁完全进入一个“游刃有余”的境界,这就是艺术的极高境界。宋代大诗人苏轼颇有感触地说到自己的散文写作:“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可知也。”一切仿佛自然天成,率性而发。但我们应该看到:当率性成为一种写作习惯,率性就将变成技术的一环。
山要起伏,水要萦迴。这其实仅仅是一种创作指向。如陶潜的田园诗把你带入一个自然和谐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生命活力,一切也许是习惯了日常生活方式的人们视而不见的。陶潜提供了文化的隐秘后花园;李清照别称“李三瘦”,因为她创造了三个千古流传的关于“瘦”的诗句,她让写作变成一种情趣化和情绪化的发韧地;而鲁迅的小说则将中国人的劣根性作了一次文本意义之外的解剖……“诗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而不是筛去或者消除它,在于保留歧义,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语言……同时建立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了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利科语)对文本的释读的乐趣,建立在我们对文本带来的审美可识度和模糊辨别性的基础之上。这方面,阅读者同样也是审美创造者和发现者。
相传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有一次和友人游南镇,一人指着山间的花树问道:“此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是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说明了艺术的创作过程至少有两个环节:一是艺术创作的技术过程;二是审美阅读的见证介入过程。文本产生的意义就在这两个过程的相拥或交织中呈现。
但由于文本在制作过程中,通常作者会涉猎并追求不同于他者的生活经验、奇思怪想、个性特征、艺术追加、语言再造等功效,那么,这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