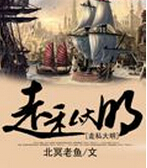常在河边走-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水里温柔地展开。只要他出现!她愿意把自己出卖一万次,只要他现在出现!哪怕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哪怕是被打入巴士底狱,只要他出现!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别让她在等待中老去枯萎。”吧里响起了田震历尽沧桑的歌声。叶铃的心口被剁了一下,疼痛象水里的涟漪越播越大,她把头低了下来,眼泪流到了茶杯里,碧绿的叶子优雅地翻了一个身。“这欲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呀……”他不会来了。
并不是很久以前,可是怎么象有一万年了呢?
当时“巴黎快车”刚刚开张不久,叶铃经常去一个小巷子里的书店买书。其实她也不常买,她习惯于绕着书架一圈一圈地走,她随手抽出一本看看作者的照片又放回去。她尤其喜欢看女作家的照片,她贪婪地把眼睛俯在她们的脸上,她要找出她们眼角的每一根皱纹,口腔里的每一颗虫牙,做作的笑容和无耻的虚荣心。她甚至要找出她们脸上遗留下的纵欲的痕迹,有时它明显得就象三伏天里的蝉叫。她看林徽音。美艳女子林徽音,风流才子徐志摩,印度智者泰戈尔,一时传为佳话。她更喜欢中年时的林,就象那句著名得快烂掉了的话:“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年轻时的林,美得有些轻率。叶铃走走看看,她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走出书店,在拐弯处她发现了一家新的酒吧,它从外表看一点儿都不显眼。它看上去甚至是灰扑扑的,宛若一个关在冷宫多年的清代宫女。它的招牌却挺大:“巴黎快车”。进去一看,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里面布置得象一列小小的老式列车。古朴的木椅子,窗子上画着风景,田野和塞纳河。玲珑的书架底下加了小轮子,戴着白围裙的小姐可以推着它翩翩起舞,供人随意挑选书本。书决不白看,这里的饮料比别处略贵,而且读书比说话更容易口干舌燥。
叶铃在塞纳河边坐了下来。她要了一杯简单而便宜的绿茶,十块钱一杯。坐在家里,我可以喝一万杯,这种茶,她想。她的脑子里随时会窜出一些比较经济学的想法,很多时候她被自己的实际和冷酷吓坏了。两个小姐挺漂亮。两株清新的小白杨。不知道会落在哪个臭男人的手里。书架推到她的面前,她胡乱地挑了一本小说,是一名女作家的,《嘴唇里的阳光》陈染著。里面没有照片,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她闭上眼睛想象陈染的形象,对了,她瘦弱而苍白。第一个乱伦的故事讲得不错,“我”就是又一个俄底浦斯,父亲睡了“我”,“我”又把他儿子睡了,可悲的是“我”不可能知道他是他儿子,可笑的是命运一定会让“我”知道他是他儿子。随手一翻,这个美丽而悲情的故事在叶铃的脑子里就演化成了这么一个枯燥的玩意。叶铃叹了一口气,心想恐怕我是老了。
这声气叹得有点重了,书吧里另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除她之外的顾客抬起了头,迅速地看了她一眼。他坐在田野边,田野是金黄色的,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叶铃本能地不喜欢男人穿白衣服,但这个男人着白实在是好看。他把头发全部梳到了后面,换了一个人恐怕就象黑社会的老大或老二,这种发型却使他全身透着贵族气。他的眼睛是细长的,有一丝微弱的笑意,增加了几分性感。他有两块微微浮出的颧骨,那是画龙点睛之笔,在他温柔的目光下凭添了适度的冷酷。因为冷酷对男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嘴角线条分明,只是颜色略微有些发乌,有点象韩国女子时兴的唇膏的颜色。
叶铃的眼睛一向是很毒的,十年前给她做过一条蹩脚的裙子的裁缝十年后走在大街上她一眼就能认出。阿朱曾说过她应该去国家安全局工作。他是吴相吴主任。绝对不会错。他脱掉了虚伪的白大褂,他改变了发型,他坐在这装腔作势地看书,他是吴相。叶铃掐指一算,不对呀,今天是星期三下午,这个大忙人怎么会坐在这里,这太奇怪了。附庸风雅,老婆吵架,员工内讧,绩优股套牢?她又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他的面容很平静,她的心里很乱。她又瞟了他几眼,他有点发现了,被迫朝她礼貌地笑了笑。他笑得让她乱了方寸,连他的笑也有一股贵族气。她看不下去书了,只是神经质似地一口接一口地喝茶,她的神情一点也不美,她把茶当作了阶级敌人。她产生了幻觉,这辆车开起来了,小姐告诉她这个男人将在巴黎下车,小姐说你呢?我?我在前一站。但是她开始犹豫了,也许我也应在巴黎下车?
他在跟一位小姐低声说话,她觉得他在用眼睛抚摸小姐白嫩的脸。奇怪,看过成千上万女人的下体之后,他居然还对女人的脸感兴趣?她坐不住了,屁股有点火烧火燎。他当然不会认出她,再眼毒的屠夫也不可能辨认出他宰过的母猪中的一只。她,一个年近三十的无聊女子,竟然对一个只冷眼看过两次的中年男人萌生了一点儿女情长,这是对还是不对呢?叶铃啊,你还是在前一站下车吧,她对自己说。
没想到吴相也在前一站下车了。叶铃看见他举着酒杯朝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她慌忙把头低下,也许他是去上厕所?上厕所拿酒杯干吗?他确实在看着她,叶铃慌得脑袋都木了,差点儿把手中的茶杯打翻。他带着一股迷人的气息在她眼前坐了下来。一瞬间叶铃觉得自己一定是搞错了,这个男人肯定不会是吴相。他不应是这样轻浮之人,她也不至于漂亮到能让吴相这等老于世故的人屈尊向她套磁。
“你为什么叹气?”
叶铃象个傻子一样看着他,这句话问得太可笑了也太温情了。
吴相啜了一口酒,笑眯眯地望着她,等着她说话。
“没什么,纯粹是生理上的。”叶铃的脸红的象火烧云。
“你长得很像我过去认识的一个女孩。”
这句话听起来又太熟了,简直缺乏一丁点儿创意。世界瞬息万变,美国人敢炸大使馆,李洪志敢吹自己能把罗锅拉直,你说这磁套得是不是太平庸了?
“是吗?她现在在哪?”
“在太平洋某个海岛过群居生活。”他转动着手中的酒杯,姿势相当漂亮。
叶铃暗想我是不是该告诉他我知道他是谁,这样做可能会有两个后果:让他感到难堪;让他对她有进一步的好感。至少他们的谈话可以继续下去。我竟想取悦于他?叶铃恨不得煽自己两个耳光。叶铃很怕与陌生人交谈,她宁愿到码头上去拉三天板车也不愿为了找一个话题能扯到对方祖宗的坟头冒的是什么烟。冷场突兀地衬出了水在她食管里挺进的声音。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拉长,锯得她心头一阵阵发麻。
“为什么是‘巴黎快车’?”她没话找话地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吴相细长的眼睛放出贼亮的光来,叶铃联想到他给她作检查的时候冷漠的表情,怀疑吴相哪根筋搭错了。
“二三十年代的巴黎是文化上的耶路撒冷。那时候的巴黎,怎么说呢,一个砖头掉下来砸到了三个人,能有二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巴黎有世界上最美妙的时装,酒,香水和思想。在俄国有知识的人都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以说俄语为耻。每天开往巴黎的列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德国,俄国,美国。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街上跟你打招呼你千万不要惊讶,他正在去赌场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想,走吧,我去巴黎吧,在那儿我的梦想会遍地开花。
下面这个故事有点奇怪了,它的来源是一个女人的日记。有一天一个外省女子跳上了一辆开往巴黎的快车。她有点象包法利夫人。她生活在外省的农村,读过一些书,脑子里塞满了巴黎的各式各样的传奇。她有很多想法,她渴望成为某个沙龙的女主人,某个剧院的女演员,乔治。桑式的女作家。她想喝酒,抽雪茄,象男人一样说粗话,从一个聚会奔向另一个狂欢,夜夜笙歌。她长得一般,好在她很年轻,十七岁,她的皮肤很白,透着少女的红晕。她没有多少钱,日积月累的零用钱只够置办一身不够体面的行头和一张末等车厢的车票。车厢里挤满了人,充斥着难闻的人体味,她看到有和她一样坚定而又茫然的姑娘,有留着长头发的艺术家,满身酒气,胡言乱语,他们粗野地看着她,发出古怪的笑声。在恐惧,兴奋和饥饿中她昏倒了。
车厢里一片混乱。很快她被好心的人们抬到了头等车厢。这里整洁清新,甚至能闻到田野的清香和塞纳河水的味道。姑娘脸色煞白,没有苏醒的迹象。这时有一个老人站了起来,他缓缓地走向这个女子,他用手摸了摸女人的额头,回座位取了一瓶威士忌。老人中等个头,留着整齐规则的长胡须,他的半边脸奇怪地凹了进去。他用一种平缓的语调对众人说她没有什么危险,只是暂时的休克,很快就能醒过来。他的法语不太好懂,带着明显的德语口音。姑娘很快醒了,她困顿地睁开眼睛,首先寻找她的箱子。然后她看到了这个老人,在他的对面还坐着一个女人。老人叼着一支雪茄,他的眼睛不大,却放出深遂的光。他穿着深色西服,白衬衫,举止优雅。他的同伴也上了年纪,但她的神情能让你在一秒钟之内就遗忘了这个事实。她的眼睛很大,里面闪烁着智慧和热情。她披着俄罗斯披肩,白头发高贵地垂落在肩上,她的身上笼罩着神秘的岁月的气息。她是一个你永远也别想忘记的女人。外省女人羞涩地向老人道谢,他们礼貌地问她去巴黎做什么。她用了一句时髦的话来回答,我去找点什么。神秘女人慈祥地看了她一眼,也许是这句话使她联想到了她自己的少女时代,她当时十九岁,一种不可思议的冲动把她带到了罗马,把绝望的爱情种到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的心中。他们三人没有过多的交谈,因为老人有些疲乏了。车快要到巴黎了,外省女人胆怯地问她是否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给这两位尊敬的老人寄上一张卡片。她在本子上写下了“弗洛伊德博士教授诊所维也纳X街X号”以及“莎乐美哥廷根XX信箱”。车到站,他们分手了。但这个外省女人有一种直觉,他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暂且管这个女人叫芒果。芒果来到了巴黎,她有一个远房亲戚,不太穷也不太富,很快这个老女人就不能容忍芒果这个毫无生产力的女人了,她面临着被踢出门去的危险。在巴黎象她这样的女人太多了,姿色平平,出身寒门,读过一点福楼拜,曾狂热地爱过于连,她们总觉得一夜之间变成伯爵夫人这样的好事会落到自己头上。芒果也曾遇到过几个男人,但很快发现他们比她更穷。看来她只能去当茶花女了,而可怜的茶花女至少还有亚芒。这时她想起了巴黎快车上的两个人。其实她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她是个智力很平庸的女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一般女人少有的强大的本能,一种巨大的激情将她点燃了。想让她老死在穷乡僻壤,做梦吧!以她简陋的知识她是不可能知道那两个人是谁的,但她仅仅凭着嗅觉就意识到了命运已经开始向她微笑了。
她对老女人说我要回家了,请给我车票钱吧。这个消息让老女人笑逐颜开,她极其慷慨地掏出了钱,比芒果索要的还多了几个子。她买了去维也纳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