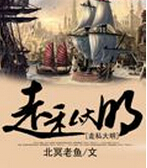常在河边走-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悠悠扬扬地降落在他们中间,他修长的手摩梭着她有点散乱的头发,激情在回忆中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芳香,她有力地吸吮着。在下山的时候,她兴奋地跳着把脚扭了,她疼痛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吴相连忙跑到她的身边,帮她脱了鞋,他轻轻地在她的脚踝上吹气。这真是迟到的祝福啊。
阿朱见到她,也大吃一惊,说:“铃铃,你的变化好大啊,知道吗,你就象怀春的豆蔻!”
叶铃懒懒地应了一句:“是吗?我也觉得自己是在梦中呢。”
阿朱举起五个手指在叶铃的眼前晃着,“你是叶铃吗?你鬼迷心窍了?”
叶铃突然睁大了眼睛,抓住了阿朱的手,“阿朱,可怜可怜眼前这个不幸的人吧!”
阿朱咯咯地笑了,“不幸?是的,我还真没见过比你更不幸的人呢。一个幽灵,一个不幸的幽灵来到了我们中间,它是谁呢?”
这时叶铃和阿朱都没想到有一天阿朱也会被卷进去。其实从这天开始,阿朱对吴相这个人已经产生了好奇心。她从未见过叶铃这样。这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叶铃的眼睛每天都闪闪发光,象一只波斯猫;她的面颊似乎是被烧得深陷下去,只留下两朵淡淡的红云,这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也不能说她变美了,不过她的身上确实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光芒。她就象干木耳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滚烫的热水泡得乌黑发亮。她整天不是在沉思就是急促地走来走去,如果打断了她,她会回报一个从遥远的世界带回的微笑;她的声音也变了,变得娇弱无力,可是在这种娇柔里你分明能感觉到一种因亢奋而拉得很高的颤音。她身上所有女性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滚滚的春雷催醒了。“这样,也太快了吧。”有时她手里捧着一本书,会自言自语地冒出这么一句话。她觉得自己的世界跟以前是完全的不同了,以前她是在黑夜里行走,她哭泣和呼叫声都被那深沉的混沌吸得一干二尽。那是多么漫长的夜啊,她惊讶自己竟然忍受了那么多年,而且如果不是得以遇见了他,她就还将继续下去,无怨无悔、无言无息地衰亡下去。想到这,她的眼里就满含了泪水,吴相,我是多么地感激你。因着感激,她对吴相的爱便更浓烈了。
吴相这两个字就足以让她全身发抖。她的眼、口、鼻、耳各种器官都对和他有关的一切变得极度的敏感,在路上随便遇见的一个男人只要和他长得有一丝相像,就会让她的心咚地一声跳得老高。她开始收集关于他的一切资料:他的书、他的专栏文章、报刊杂志上介绍他的文章。她把书扉页的照片小心地剪了下来装进镜框,摸着、看着、亲吻着才能入睡。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她发现他的名声的走势越来越强劲,他的名字前面一律加上了“著名”两个字,于是她感到了莫名的恐慌和醋意。没有缘由地她就将自己放逐到无边无际的嫉妒的炼狱里了。这个“慕名”象一把刀一样稳稳地插在了她的心口上,它会给他带来多少女人呀,她快要被自己活灵活现的想象击垮了。现在,她希望他什么也不是,或者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一个打着凌辱烙印的囚徙,她将象圣母一样吻遍他身上所有鞭打的痕迹,他们的泪水会交织在一起,浇灌出一朵最美的盛世之花。
阿朱终于可以反戈一击了,她斜眯着一只眼,说:“叶铃,还记得你过去对我说的吗,爱情给了我们很多,可它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更多。怎么样,轮到你了。”
叶铃苦笑着说:“亲爱的,原谅我的浅薄吧,原谅我的幼稚吧。对一个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多一点宽容吧。”
“幼稚?我倒觉得现在的你才是幼稚的。你怎么越活越没记性了?总算轮到我说你了。我觉得你很危险,说真的。他都已经结了两次婚了,他四十多了,你指望什么,指望他再离一次婚,再结一次婚?做你的大头梦吧。他对你真的动了感情吗?八成也不过是玩玩吧。现在两条腿的高级流氓比四条腿的狗还多。你不是总说吗,最没心没肺的就是这帮小有成就沾沾自喜的狗日的知识分子了。你还说过什么,宁愿养一只阿猫阿狗也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感情。这些都是你的原话吧。叶铃同志啊,三思而后行,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有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回头总是岸。”阿朱越说越激动,脸都红了。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唉,等等,忘了问了,你们睡了吗?”阿朱直直地看着叶铃,仿佛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叶铃扑哧一下笑了,“你紧张什么呀?我都残花败柳了。不过,老实告诉你,很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叶铃笑得太早了。我们头脑里的意识形态一再地教育我们: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有好下场的。古往今来的历史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阿朱在读报时,看见了一段话,是五七年反右时中央处理丁玲问题的一段指示:“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流氓性。不能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这段话与第三者无关,不过阿朱还是把它读给叶铃听了,她觉得它有些精辟,也适用于叶铃。
知识分子无疑是最软弱、最自私的阶层,他们是最容易跪倒在名利和权力的脚下的,他们需要不懈的灵魂的改造。当然,早在几十年前,伟大的毛主席就有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并将此阶级不断地推到审判席上。中产阶级则是最伪善的阶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就真的是不可救药了。那么吴相是谁,他不就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吗?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他迅速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新贵,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多的指责他,他的寻花问柳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沦落成一个道德人,他还保持了卢梭笔下自然人的一些率直秉性。是啊,谁能说昆德拉的托马斯不可爱呢?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句话让男人拍手称快,手舞足蹈。女人是不是也该给这句话当头一棒:没有婚姻的爱情同样是不道德的。
爱的目的就是爱。叶铃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也可以说她以为她是这样想的。想一想吧,连波伏娃这样的女性最后都不可遏制地想要与花花公子萨特携手走向那美丽的坟墓!谁也无法逃脱那永恒不变的人性。对女性的歌颂无非是:为了爱,她们宁为玉碎,在伟大的爱情面前,她们勇敢得象老虎,骄傲得象狮子;男人呢,则是苟且的蝼蚁,缩头的乌龟。此言差矣。因为女人的全部生存就是爱,女人的信仰是爱,女人的宗教是爱。而男人为了事业不是也象女人为了爱情一样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吗?
叶铃对别的就不再感兴趣了。她等待着。或者上上街,去美容院,小姐的手在她脸上抚来抚去,她闭上眼睛感觉到暗香浮动的女人水一样地从身边流过,她的嘴角泛起一丝惆怅,她压低了嗓子说:“小姐,这才是人的生活啊。”她又去了桑拿室,一个人。她把自己蒸得透不过气来,快要昏厥。她躺在木凳上,披头散发,沉沉睡去。她觉得痛苦到要遗忘。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她一个人来承担。她被这场爱庸俗化了。她感到爱到不能再爱了,要死,必须死。
分手时,吴相用手摸她的脸,说,等我给你打电话,三天后。所以她等待着,脸上还留着手的余温。她梦见一个人被等待这个动作杀死,它长着她的脸,手指是黑色的。她不知道在吴相那三是个虚词,可以是五,也可以是七。期限过了,她变得极度的狂躁和自卑。感激和怨恨是她心头的两朵花,同时开放了。他欺骗了她吗?还是她做错了什么?她是不是不该回应他的吻呢?是她表现得过于热情了吗?她是不是应该把他的嘴挡开,把他的手打开,义正辞严地说:“您?怎么可以这样?”她设想她在他怀里的样子,她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丑,不能再丑,不能再贱。她也不能知道他是谁,只是爱,不能死,也不能活。
他只是忙。忙得颠三倒四,不亦乐乎。吴相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规律:他在工作和女人之间的转换就象四季循环一样自然和流畅。爬完山回来,灵感轰然而至,他和宝宝酣畅地洗了个鸳鸯浴,然后坐下来为两家杂志写了两篇专栏稿。总有做不完的事。谈不完的情。不厌倦吗?有意思吗?睡觉前,儿子一脸严肃地找他谈话,“爸,我心里挺别扭的。我恋爱了。”事后,他照了照镜子,他一直都很喜欢照镜子,他心里也挺别扭的。他的儿子有女朋友了,他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叶铃。”他轻轻地喊了一声。他在镜子里看见了叶铃,比她本人要美。他用两根手指撑开眼角的皱纹,朝自己做了个鬼脸,是的,他还要再见到她。不错,刚刚开始。叶铃和吴相的交往总有些拖泥带水。叶铃觉得这场爱情越来越象老牛拖破车一样,不能忍受。最初的甜蜜过后,她身上某些黑暗的本性又复活了,它们总是叽叽喳喳地嚷着:“不,不能这样了。”他们第一次做爱后,她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崩溃。
吴相太了解女人的心理了。每次都是要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他准确地扔给她一根救命稻草,那快要死灭的火就呼呼地烧起来了。她就在理智与情感拴起的钢丝绳之间跑来跑去,直到她将两者都彻底失去。他给她打电话,一开始却哼哼哈哈,保持着一种不言自明的暧昧和自尊。叶铃就主动说:“吴相,你是想见我吗?”吴相说:“臭美,谁想见你,你以为你是谁?”叶铃象哄一个孩子一样,“好吧。好吧。是我想见你,那我请你吃饭吧,礼尚往来,肯赏脸吗?”吴相故意顿了一下:“好吧。算你脸大。”
吃完饭以后,吴相把她带到了一个旅馆。吴相甚至没有征求她的意见,这点让叶铃有些不高兴,又有些说不清的快乐。吴相在门口悄悄对她说:“我先上去。过一会儿我把房间号呼在你的机子上。听话。”她又一次被扔进了等待之中,只不过这次是具体的,诱人的,可以逃脱的。她有些犹豫,她要不要惩罚一下他,也让他尝一尝被抛弃的滋味。这个念头大概只在她的脑子里停留了一两秒钟。她不敢冒这个险。她上了楼梯,腿有些软,她下定了一个决心,不,我不跟他做爱,绝对不。无论怎样,也不。她已经来到了房间的门口,她站定了,想走已不可能。
吴相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好,就锁了门。她不知道是站还是坐,紧张得象二八少女,脑子都糊涂了,唯一想的就是要上厕所,非上不可,吴相朝她走过来,她一着急就说错话了:“别,我想先尿尿。”吴相把她抱住:“傻丫头,这么没出息,我陪你尿。”诺曼底登陆一样,全线溃败,哪里还有防线,她的嘴里唯一能吐出的一个词是:“坏蛋。”
非常野蛮。什么也回忆不起来,非常可怕的爱与美,他的力量很大。想到他和身体,叶铃的语言是断裂的:必须、奴隶、只能如此、献身、杀和被杀。他了解她,他打开她的身体,把自己放进去,用她最喜欢的名字呼唤她:小婊子、小骚货、小贱人……。她为自己的快乐而羞耻,她想到有一天她一定会对他说:“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耻辱。你看见了吗,我多么幸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