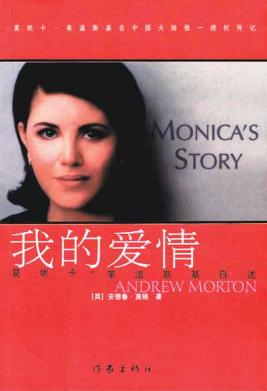爱情集训营-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胳膊化作肉泥天女散花般地洒向江面,点点血迹将船舷烙上朵朵梅花。那梅花,在五月的阳光里渐渐变得暗红,继而黑紫……然而,爱情是一济迷魂汤,娘的飕飕凉风怎么也吹不醒渐入魔境的玉竹,直到一声炸雷似的空炮才惊醒了这对耳磨厮鬓的鸳鸯。木木出事了,一条胳膊炸飞了。玉竹一瞅见那褴褛的袖管和白惨惨露出了半截断骨的残臂就昏厥过去,任凭娘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和一个落难的右派稀里胡涂地结了婚。洞房花烛夜,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把玉竹震醒了。她撇开新郎发疯似的跑到洣江河边。河边上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木木炸塌了自家的小土屋,摇着那叶扁舟顺着洣水河飘然而去,任玉竹喊破了嗓子也不回头。
八年后,我来到柳家庄教书,了解他们一些情况,也见过玉竹。
那是一个九月的下午,一个中年妇女为了女儿的学费找我说情。我深深地打量着这位不到三十的女人,蜡黄的脸泛着几圈惨淡的白晕,两眼暗然无神,额上烙着几绺多舛的横纹。这人便是玉竹,与我想象中的美女完全八杆子打不到边。听说,她婚后也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丈夫是个老实人,单位上划右派还缺一个指标,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去顶数,他就胡里胡涂地把这顶帽子给戴上了。再来一次运动就发配到这穷山恶水改造。所幸的是这里民风淳朴,没有人给他另眼相看,相反还因祸得娶了个漂亮媳妇。因此,小俩口是妇唱夫随,琴瑟和谐。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柳琴。可是好人总不能一路平安,柳琴出生不久,丈夫被派出修水库,在采石场,从二十多米高的山崖上摔了下来,造成高位截瘫。一家的生活重任全部一下子压到玉竹身上。玉竹身心疲惫,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安顿丈夫的生活,白天则要顶一个男劳力去忙外面的活,晚上大家都上床休息了,她还要替丈夫洗屎洗尿。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个三十不到的少妇憔悴得象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尤其是娘死后,她的整个精神支柱全垮了,有好几次她想一头载到洣水河去一了百了。可是她走后,女儿和丈夫怎么办?只好咬咬牙挺了过来。
玉竹见我没作声,连忙说:“老师,我知道学校经费也紧。可我一时半刻实在是想不出法子。家里有是有窝猪崽,可是才上潲,这会卖了实在可惜,我……”她的头低得很低,几乎要哭泣的样子。我的心软,连连点头说没问题。她脸上这才有了喜色,连忙从身边拖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琴儿,还不叫老师?”
“老师。”柳琴接了书,很有礼貌的向我鞠了一躬。然后,母女俩相视而笑,笑得是那样的甜。我鼻子一酸,赶紧调过脸不去看她们。
柳家庄这鬼地方,苦虽苦,人丁却很旺盛。屋挨屋,房挤房,抬头一线天,低头一条巷。学校位于小巷的中段,设在柳家的大祠堂里。这祠堂废弃了多年,也没有牌位。但柳家庄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好事歹事都要到这里点一把香火,烧几束纸钱,故显得特别阴森。白天还好说,学生穿梭似的热热闹闹,一到晚上,两个老师,一个是民办,回家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凄凄切切,时常让人生出莫名的恐惧。因此,柳琴能在放学后多逗留一会,做做当天的家庭作业,这在我是求之不得。
柳琴很聪明,我教过的东西总能很快记住,而且捏得一手好泥活,什么样猫呀狗呀,在她的手里一转便栩栩如生,有时甚至比真的还有灵气。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学生。她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她不想回家,她怕她爸爸。她说她爸爸脾气大,经常摔东西打妈妈。她们好害怕好害怕。
一个秋风飒飒的黄昏,我独自一个人在江边徘徊。潇潇的江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霭,斜阳拖着疲惫的身子静静地卧在江底。突然,一条小船飘然而至。船舱里钻出一条黑影。这是一个蓬头垢面的黑汉,满脸的络腮胡又粗又密,象块锄头从没光顾的茅草地。一双眼睛阴森而又精锐,尤其是那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的空袖管让人产生出许多神密恐怖的联想……
“木木!”我惊叫一声。
风很猛,船晃得厉害。木木挟着一个包裹,晃着空袖,走下船来,将包飞快地塞给刚刚走到河边的柳琴,转身跳上船,很快地消失在迷濛的江雾之中。
柳琴懵了,抱着包裹战战兢兢地走到我的面前,好象课堂上搞了什么小把戏又当场被我捉住了。我接过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儿童用品,其中那种深筒靴在柳家庄当时还只有支书的小三子穿过。
从此以后,柳琴放学后不再在学校逗留,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正想问个究竟,玉竹来了。这女人似乎比以前更憔悴了,眼圈那片灰蒙的云翳也比以前更加暗了。
“家不走运,那窝猎崽瘟了,一只只全丢到洣江河里去了,没买半只毫子角。这是我卖南瓜凑的钱,凑了五墟才凑齐三元五角钱学费。”玉竹叹了一声,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皱巴的分票和哗哗响的硬币塞到我的手,说:“老师,你数数,看没有错。孩子她爸说,他可以不吃药,一家人可以不吃盐,学费一定得交。”
我双手捧着一大堆分票硬币,眼睛湿润了,想说点什么,可一句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我带着这一大把钱问到了柳家。柳琴叫了声:“老师……”就哽住了,两行热泪从脸颊上挂落下来。玉竹双手在围裙上擦擦,尴尬的说:“老师,怎么会是你……你看真不好意思,连个坐的地方都有没有。”她丈夫躺在床上,灰蒙着脸,欠了下身子,瞟了我一眼,算是和我打过招呼。我的心一凉,知道此次家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我那振振有词的劝学宏篇远不及床上病人的几声惨淡的呻吟。但既然来了,我还是得说。我说,我知道你们家的实际困难。我已经向大队学校申请减免柳琴的学费,实在不行我可以给你们垫付。我说,柳琴这孩子太聪明了,如果就此辍学就真的太可惜了。我说得很快,生怕被人打断,没有勇气再说下去。玉竹哭了,柳琴也哭了。只有床上的病人紧紧地闭着双眼,似乎睡了。我想:“完了,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我站起身准备回学校去,那人睁开了眼,挥了挥手对柳琴说:“明天跟老师去吧……”
缺了一大截课,柳琴学得很费劲,我便到柳家去补课。玉竹自然是千恩万谢。她丈夫依然冷漠,有时竟看也不看我一眼,倒好象我欠了他什么。柳琴很快活,每天总是认认真真地听讲,踏踏实实地完成补课任务,然后又缠着我要我讲一些初中高中才能学的天文地理知识。一天,她变戏法似的搬出一包包糖果副食一咕噜塞到我的怀里给我吃。我不竟有些犯傻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般人家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尝得一两回。这个连三块五角钱学费都拖欠了大半个学期的穷苦人家怎么会有钱买这玩意儿吃。这个谜团让我苦苦思索了三天。第四天,谜团才解开。
那天,我一走进柳家的院落就听见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进屋老远便看见柳琴偎在一个壮汉的怀里。这不是木木吗?他推了一个和尚头,头发胡须一扫而光,人显得很精神,要不是那空荡荡的袖管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柳琴见我来了,连忙飞快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走到木木身边,替我们作介绍。
“好,好好好,听老师讲书吧。”木木拍了拍柳琴的肩,将她推到我身边,然后掏出那竿黑黝黝的水烟筒巴哒巴哒地吸着。他低着头,只顾默默地吸烟,仿佛这世界上只有他和这烟管存在。我给柳琴上了两三个小时课,他没抬头看过谁一眼,更不用说和谁说一两句话。
自此,我隔三岔五地遇到木木。据说他每天都要到柳家去坐坐,而且每次都没有空过手,吃的,穿的,用的……他从不搭理玉竹,也不招惹她丈夫,总是默默的坐会儿,抽袋烟,和柳琴说说话,然后再默默地回到小船上去。
山民们的日子象这悠长的洣水河,一天一天地平静泛味了,总想掀起点波浪什么的。木木的出现在村里掀起了翰澜大波,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什么拉帮套呀,一女事二男呀。也有同情玉竹为她袒护的,说木木本来和她就是一对,是她娘硬把他们拆散的,如今她丈夫这样了,她等于在守活寡,木木来拉她一把,有什么不可。对于这些闲言碎语,玉竹从不置辨什么。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这情形也难怪别人不说闲话,她堵得住张三的嘴堵不住李四的嘴。木木则装作什么样都有不知道,或许这正是他所期望的——他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满足。不过,木木还是走了,又一次从柳家庄神密地消逝了。
那是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滂沱的大雨似乎要把天地间一切都浇透,风凄寂的嘶鸣着,幽灵般地在都间破祠堂里逡巡。笃笃笃,有人在敲门,这种时候谁会找我?我正在狐疑,笃笃笃,门敲得更急了。我高叫一声说:“来了!”便开始穿衣起床。可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双手在大门上擂了起来。我赶紧开了门,狂风暴雨裹着一个水淋淋的醉汉滚了进来。
“木木,怎么是你?这么大的雨,你从哪里来?”
“我要走了!妈妈的,”他大声嚷着,酒气醺天。“我要走了,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狗日的!”
“别急,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我把木木拉进屋,取了干毛巾给他擦拭,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
木木一言不发。过了好一阵,他才从那堆湿漉漉的衣服里掏出一瓶酒来,可怜兮兮地望着我说:“陪我喝一口,行吗?”
我一时找不到好的法子替他解忧,只好陪他喝酒。说来也怪,他一沾酒,反而平静了。于是他边喝酒边向我诉说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下午,我去追一群鱼。这是一群大鱼,少说也有四五百斤。这些家伙很滑,我知道自己没个帮手很难吞个囫囵,可铆上了,让它们从我的眼皮底下白白遛走,还不如拿个女人的尿盆扣在头上。我跟了它们一整天,从猫岭一直悠到老鹰潭。日头下山了,鱼们争出水面透气儿,好家伙密密匝匝缩成扮禾桶大一团,剥剥剌剌的水珠儿溅得脑高。我停下船来想,要是有两个帮手,点三个炸药包,布个梅花阵,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也跑不掉。可那来的帮手,不要多想了,等那些精灵们透够了气,钻了老鹰潭。我只有顶尿盆的份儿。我把船悄悄地靠过去,断了狗娘的退路,掏出两个炸药包,一个引芯捻得很长,一个引芯捻得很短,一起点燃了。轰轰两声,水柱塌落后,江面上一片白,象秋日里沙洲上曝晒的红署片儿。我的这条胳膊累酸了,实在抬不动了,便把小漏勺绑在这只断臂上,横躺着靠在船舷上一大把一大把的兜。”
我盯着木木,望着那空荡荡的袖管,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怎么把小漏勺绑上去的。
木木半闭着眼,似乎睡熟了。忽然,他又坐了起来,把眼睛睁得贼亮,抓起酒瓶又给自己倒了解一大碗。
“回来时已是后半夜了。我有些累了,又喝了几杯,眼皮都睁不开了,正准备撒泡尿就去睡。一走上船舷突然记起一桩事来,我的睡意全跑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