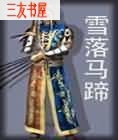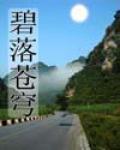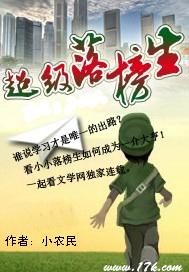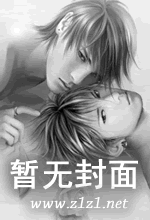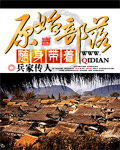黑角落-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言
1988年,我被GWU(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医系录取为刑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只身一人,单枪匹马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奋斗。10年旅美生涯,使我对美国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
号称当今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除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科技和高工资之外,还有高犯罪率。
从GWU毕业,经过较短时间的奔波后,我得到在美国监狱的一份工作。和监狱里形形色色的犯人打交道,使我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有了一个与其他人相比较为独特的视角。我希望能从自己的特殊角度,对美国社会及社会问题做一个客观的反映,使读者能从不同的侧面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美国。
在美国监狱工作,经常遇到的冲突是犯人和犯人之间、犯人和狱警之间的冲突。犯人之间的冲突大多是穷极无聊的寻衅闹事,或因暗中的毒品交易,或因同性恋之间的争风吃醋引起。而犯人和狱警的冲突则是管与被管,双方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平时狱警以监规为律条监管犯人,更多的则是为犯人服务,一旦发生冲突,出现犯人受伤、死亡等事件,不论原因如何,倒霉的往往是狱警。轻的被指责没尽到看守之责,重的则会被指控侵犯人权,甚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在美国这个“人权”呼声最高,最推崇人权的国度里,犯人的人权状况是人权组织关心的焦点,犯人的人权因而被大大地强化了。狱警和监狱动辄得咎,被媒体和社会舆论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监狱方面为平息社会公众被煽动起的愤怒,经常拿狱警开刀,用开除公职或处分来迎合公众。这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切身感受到的最不公平的一点。事实上,说到人权,在监狱中的所有人里,那些在监号值勤的狱警才是最缺乏人权保障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权并非广义人权,而仅仅指人身安全保障的人权。为了体现文明执法,为了约束狱警的行为,在监号这个监狱中的第一线执勤的警员不允许佩带任何武器。他们必须手无寸铁地面对那些秉性凶残、身强体壮的犯人,包括面对因特级警戒监狱人满为患而疏散到中级警戒监狱的杀人不眨眼魔王般的重刑犯。这些犯人身上还常常隐匿着他们自制的各种杀人凶器。狱警一旦在冲突中受了伤,不论伤势有多重,被允许休养的时间是有限的,超过时间要用自己的假期来补,假期用完还不能上班,则停发工资甚至有被解雇的可能。各种传媒中常见连篇累牍为犯人鸣冤叫屈,为犯人张目,对警方和监狱方面则口诛笔伐的大块文章,却从来见不到对因公受伤,甚至殉职的警员表示尊敬的赞誉文字。也许是出于“保护弱者”的动机吧,人权组织把落入法网失去自由的犯人统统当成了需要保护的“弱者”,似乎忘记了他们落到这一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曾经强悍凶残地杀人越货,他们不过是被关进樊笼的蛇和狼!当然,我决不是主张歧视虐待犯人,但一个社会的主流呼声,对犯人的人权状况兴趣盎然,关怀备至,而对维护着社会治安,保护人们充分享受安全生活的警员们的生死却置若罔闻,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在美国,大概许多人认为,警察拿了那份工资,就该干那份危险的工作,似乎一切人身的保障、家庭的幸福全都被那份工资所包含的金钱数目所量化了。但人的生命,一个家庭的完整,难道能和任何数量的金钱画等号吗?
我的一个同事,并无任何过失,仅仅因为运气不好,赶上两个重刑犯企图越狱,他一时不慎,相信了犯人的谎言,打开了独居监号的门,想去救那个装病的犯人,却惨遭犯人的杀害。葬礼上,他的年轻的遗孀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灵前哀哀痛哭。在场的每一个警员,兔死狐悲,无不泪满襟衫。事后,那两个犯人虽然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可是那个警员已永远失去了生命,他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女也永远失去了父亲。社会对此却一无反响,这难道公平吗!
这本书决定以小说形式出现,是颇费了一番思量的。书中的素材完全来自于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有些事件有其偶然性而并不具备文学意义上的典型性,似乎写成一篇纪实文学更合适;但考虑采用真名真事如实写来,很可能对别人有所不便。我只想反映一种真实的现象,而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最终决定采用小说的形式,写成了这本似乎不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样式的小说。需要申明的是,本书采用了虚构的人名和一些虚指的地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完全不是纪实性的文学。希望读者阅读此书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去猜测书中的角色是生活中的某人。如果某人的情事与本书所述相同或相仿,那“纯属巧合”。
本书取名《黑角落》,无庸讳言,是受了美国影片《红角落》的启发。这是一部最近在美国上映的影片。从一个在中国司法部门有多年工作经历的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那部影片把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及执法人员丑化得一塌糊涂,脱离了中国的真实,只能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与《红角落》的作者相比,我的出发点与之大相径庭。影片《红角落》的“红”字是有政治色彩的,它显然缘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红色中国”相称的历史。《黑角落》的书名却无任何政治含意。之所以称其“黑”,是因为无论在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监狱总是在远离尘嚣的阴山背后,那里羁押着曾经有过各种罪恶行为的人们,的确只能用“黑暗”来形容他们的心态;而美国的监狱,无论是建筑还是人员的着装均以黑色为主,这也是我称其为“黑角落”的原因。
石子坚
1998年6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一)飞越太平洋
“请系好安全带,先生。”
李易之睁开双眼,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约摸五十开外的老空姐正彬彬有礼地注视着他。他一边心里惊叹这位空姐的高龄,一边乖乖地系好安全带。
飞机震颤着向前驶去,加速,再加速,终于腾身而起。李易之透过舷窗向候机楼望去,希望能看到大落地玻璃墙内杜迎和女儿的身影,她们一定还在那儿,看他乘坐的这架波音747起飞。一进机舱,他就曾试图看到她们,但庞大的机翼遮住了他的视线,角度不对,他看不到她们,只好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此时,他又一次向候机楼投去搜寻的目光,希望再瞥上一眼,他看到巨大的候机楼已变得像一所矮小的民宅,机场上走动的人像蚂蚁一般小,一会儿,连蚂蚁也赶不上了。大地迅速地被推远了,变成了一块大沙盘,被切成条条块块的大沙盘。
泪水涌上李易之的双眼,涌出眼眶,止不住地哗哗而下。李易之这个34岁的魁伟强壮的汉子,没有料到自己竟有如此多的泪水,没有料到这么多泪水竟会因为离别而奔涌。这是怎么了?一时间,他对自己的反应不由得有些奇怪,是因为舍不得妻子和女儿?舍不得父母舍不得家?仿佛是也不全是。一年来,不正是他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含辛茹苦,千方百计地为他有一天能坐上这架美航的越洋客机飞出国门而不懈地努力吗?他所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每一重难关不都是命运对他的留难,阻挡他跨出这一步,而他自己面对它们,不都是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排除之、跨越之吗?当他拿到华盛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使馆的F-1签证时不是满怀喜悦地接受妻子和家人的祝贺吗?怎么如今喜悦的心情荡然无存,变成一腔的落寞惆怅,甚至是悲伤。
“坚强点!”心里蹦出一句自我勉励的话,立刻又觉得有点好笑,哪儿是哪儿啊!又不是遭了重大打击,需要咬牙挺过去,出国,去美国,这不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吗?坚嘛强呀!这不是不合逻辑吗?任他如何自嘲,如何不承认自己反应的合理性,一种非酸非甜、非苦非辣却味道厚厚的割舍不下的情怀在他心头涌动着,排遣不开。他突然强烈地感到是自己对这越离越远的大地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是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自己。这力量是那样强大,以至于要挣脱它如此痛苦,如此困难。一年来,他第一次怀疑自己这抛妻别女、去国离家的抉择是否正确……
一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李易之和妻子杜迎带着不满5岁的小女儿到姥姥家度周末。午饭后,姥爷照例回房午睡,小女儿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杜迎在厨房帮母亲收拾碗筷。
“易之,你们夜大发毕业证了吗?”杜迎的大姐杜静边问边递给妹夫一个削好的苹果。
杜静是李易之在检察院的同事,工作接触中,对李易之印象很好,就把自己的二妹杜迎介绍给他。李易之性格有点内向,但思想上进,工作作风干练,杜迎身材颀长,文静内秀,二人一见倾心,遂成连理。婚后相敬如宾,夫妻间从未红过脸,小女儿津津的出生更给这小家庭带来无限欢乐。对这位促成他幸福婚姻的大姐,李易之一直十分尊重。
“发了,一个法律文凭,一个英语文凭。”李易之简短地答道。
“姐夫,你也试试考托福吧!550分就够资格到美国读学位了。将来杜迎还可以办陪读,把津津带去,多好,在国内有什么混头。”杜迎的小妹杜荣听说姐夫拿了两个文凭,立刻心直口快地鼓动起来。
“别胡扯!”岳母从厨房走出来,打断正在兴头上的小女儿,“三十多岁了,还折腾什么?在检察院干得不错,都提了两年的科长了,再熬两年三年提个处长,就行了。你爸干了一辈子不才是个处长,别不知足,出国,那得一切从头干,别看人家出国眼热,你出去,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放着稳稳当当的日子不过,去冒那个风险!”
杜荣刚要还嘴,见杜静向她使眼色,便打住了。杜静顺着母亲的话,说道:“易之当处长是有希望的,能力成绩都摆在那儿,这回又一下拿了两个文凭。”她顿了一下,向妹夫笑了笑,“不过,你的文凭还不够,还得拿个‘关系学’的文凭。易之不会来事儿。再不注意该成焦书记第二了。”
大家都笑起来,杜静说的“焦书记”可不是焦裕禄,她说的是检察院的书记员小焦。小焦自学心劲十足,拿了五六个大专文凭,就因为不会搞关系,一直提拔不上去,比他后参加工作很多年的人都提成助理了,他还是书记员,人送外号“焦书记”。
出国的话题被转移到关系学上,争执也就没有了,连李易之自己在内,全都认为他在搞关系这方面太欠缺了。可是说归说,真要他变成一个“会来事儿”,会搞关系的人,恐怕比出国还难。
转天下了班,杜荣跑到二姐家,和姐姐、姐夫商量了一晚上。李易之终于下定了决心,准备瞒着家里人,先考托福,再请易之在美国读博士的弟弟帮助联系大学。等真被录取了,再跟家里摊牌,万一不成,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李易之就开始实施他出国计划的第一步—;—;准备考托福。这包括玩命学英语和准备考试费用。当时托福考试费是29美元,按1:3比例兑换,合人民币87元,比李易之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几块钱。杜迎让丈夫别担心,只管考好托福,联系学校。决心下定了,就是倾家荡产,也得实现它。看到平时文静娴淑的妻子竟然如此意志坚定地鼓励自己,李易之感动之余,只有更加拼命去努力的份儿了。
托福顺利地通过了,接着是申请就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