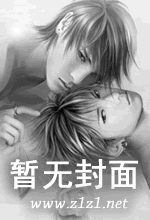21位试婚者采访实录-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梅是我一位朋友的表姐,故而我一向称她朱姐。两年前朱姐刚到北
京时朋友曾托我为她物色个男友,并一再强调没什么条件,只要有北京户口,
人老实本分即可。因为朱姐条件不好,当时又已经32 岁了。虽然我不太明
白堂堂一个职业律师如何沦落到“困难”至此的地步,但也确实“对号人座”
的为其张罗了一番,接连介绍了两位男士轮流登常起初男方听了朱姐的条件
后都颇为满意,但双方见面后不久两个竟都打电话表示歉意,理由是“这阵
子很忙,慢慢再说吧!”亦或干脆就是“怎么那么别扭,我可不敢要。”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其实最别扭的将要是我,因为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措辞将男方
的这种意思婉转地告诉朱姐一一像她这个年龄的独身女人在这方面往往很自
尊,也很敏感。
朱姐的反映却出乎我意料,我刚一开口她便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很不
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岔儿说:“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哪就那么容易,一碰一个
准?第一个我还没看上他呢,第二个条件还不错,可就是一笑就嘴歪,没啥
可惜的,没事儿,没事儿。”俨然需要安慰的是我而不是她,东北女人的豪
爽劲儿在她举手投足问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我真是有些诧异了:“按说她不
应该嫁不出去。”
后来,朱姐的呼机丢了,我们的联系便从此中断。在这个忙碌的都市
中,人和人的交往实在有大多的偶然性和阶段性,曾经相识的两个人往往匆
匆相遇、停留片刻之后便又擦肩而过。各得其路,以后很难再见,我把朱梅
也划入此类,渐渐忘却了。
不料今年教师节的那一天,朋友突然通知我晚上来接我去朱姐家——
朱姐请我们吃饭。我不禁问道:“怎么,朱姐成家了?”朋友很无所谓地笑
道:“家是有了,只是还没成。”出于一种职业特有的敏感,我似乎明白了什
么,只是还不敢确认。
朱姐的“家”在北京东郊一条典型的老北京的小胡同里,一个小小的
院子里住了房东和房客三家人,朱姐的房间在阴面,虽然面积有十多平米,
较大一些,但却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很清冷。房子里因为东西太少,竟显
得很宽敞。一张四腿木桌,一只单人沙发,两张单人木床,各占一角,几只
皮箱整齐地放在床底下,除此别元它物,简单地宛如一间乡村小店。这到有
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说实话,我以为自己看到的会是一个锅碗瓢盆、杂物
堆积,地中间摆着一张双人大床的“家”,而决非如此。朱姐似乎看出了我
的想法,很轻描淡写他说了句:“快一年了,走着看吧!”“他今晚回来吗?”
我问。“今天教师节,他们教研室都去龙庆峡了,明天回来。你俩今天都别
走了,好好聊聊。今天也是我来北京两周年纪念日。”这时我才想起来,两
年前的教师节那天,正是我和朋友一起接朱姐下火车的。那是她第一次来北
京。
院子里突然一阵噪杂,朱姐很抱歉他说,由于地方小,他们只能借用
房东的炉灶做饭,可今天房东的儿子、儿媳也回来了,看样子轮到我们做饭
没时候,还是出去吃吧。
我知道朱姐的收入不高,不想让她破费,建议订几个盒饭,我们就在
小屋里边吃边聊,我隐约觉得,这个小屋远远没有它的表面那么简单。朱姐
略想了一下便同意了,她说有朝一日她一定要体面地补上这一顿。
当胡同口小餐馆的伙计将盒饭送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都没有饿意了,
因为朱姐的故事刚刚开始:也许你们都不理解为什么到了我这个年龄还非要
往北京挤,和年轻人争这口饭。其实我来北京的目的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为
了赚钱,也不是图发展,我只是突然想成家了,想来这儿遇个合适的人,咱
也正常的过几年日子。呆在哈尔滨看来是没这种可能了,土生土长地在那儿
过了三十多年了,生活的圈子基本定型,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来来回回就
那些人,我看不上他们,他们更看不惯我。
直到三十多岁还不结婚的老处女在那种地方你想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什么希奇古怪的事都能往你身上安,地方越小好事者越多,他们一点一点地
把你伤得体无完肤之后,翻过来还要指责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所以
我就想出来看看,北京毕竟是首都,人们的文化层次相对高些,没准还真能
找到一个家。这两年我也许是太孤独了,真的不想再一个人过日子了,曾经
有一阵子,一听到那首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就哭,不是哭泣,是放声的
哭,反正家里就我一个人,怎么哭别人也听不到。第二天发现眼睛哭肿了就
不去上班,反正干律师这行唯一的好处就是自由,我有时候能在炕上一躺就
半天,不吃不喝,像个病人膏盲的人似的。“怎么你家里是炕?”我终于忍
不住问了一句。朱姐微微笑了一下,突然放下手中刚拨了几口的盒饭,叹了
口气。
“唉,我来北京后最怀念的就是我的那条小炕,冬暖夏凉,舒服着呢!
人说破家值万贯,有道理呀。要不是舍不得那个家,也许我还能出来的更早
些。”我家的结构很简单,只有我和我奶。我奶九四年去世的,从此我就没
啥牵挂了。
我八岁那年我父母就离了婚,童年在我的印象里是在一片打打杀杀声
中过来的。父亲经常打母亲,母亲经常打我,打急了母亲就拿着菜刀往自己
脖子上比划,我就经常哭着离家出走。每次都是我奶捣着小脚把我找回来,
我至今都相信我这前半辈子除了我奶她老人家没人真心疼过我,当然除了这
屋子的另一个主人。
那时候谁家大人离婚都是件很见不得人的事儿,连学校的老师都瞧不
起你。一跟哪个同学闹点儿别扭尝到的好果子便是掷地有声的一句:“你爸
你妈都离婚了,还在那儿牛呢!”这种话对我来说真是立竿见影,我立刻就
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软了下去。久而久之我也就很少跟同学来往了,免得自
个儿找罪受。
离婚后我母亲就拿走了家里所有的细软,改嫁到了沈阳,听说后来又
生了个女儿,只是我从此再没见过她,她也从来没张罗着找过我。人家都说
母女之间有天性,离多远也隔不断思念之情,可不知为什么在我们母女之间
却没能应验。我父亲离婚不久也另娶了,那个女人很精明,变着法的期负我
和我奶,我经常和她打架。有一次她说我好吃懒做竟烧了我唯一的一本破小
人书,我也急了,抓起她的一只新翻毛皮鞋就扔进了炕边的灶火里。于是我
父亲便一脚把我从炕上踢了下去,头正好磕到门框上,当时就血流不止,至
今都留了很深的疤。
说着她撩起额边的刘海指给我们看,竟是一道一寸多长的伤口。我忍
不住轻轻拍了拍朱姐的手,也不知是在安慰她,还是示意她接着往下讲。这
时我才发现原来朱姐长了双很漂亮的手,纤细、柔软,极有女人味儿,实在
与她暴烈的性格有些不相称。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主动开口跟父亲说过一句话,何况也没有机会了,
两个月后他们便搬到了厂里分给父亲的新楼房去住了,那里离市区很远,我
从来没有去过,他们也没有叫过我。从此那套破破烂烂的旧平房里,就剩下
我和我奶相依为命了,并且一老一小一过就是二十年。在我工作之前,我们
唯一的生活来源只有两个:一是我父亲每月按时给的一点生活费;再就是我
奶捡破烂、卖冰棍挣几个钱。幸好那时我父亲他们厂效益好,收入还可以。
总之跌跌撞撞地竟也熬过来了。直到我当了律师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才有
所好转,我奶也不用再出去卖冰棍了,但我们家的摆设,布局却还是老样子,
除了一台十六英寸的黑白电视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气息。如果你想知
道七十年代哈尔滨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那么到我们家一看就清
楚了。家里至今没有衣柜,用的还是那种摆在炕上的木头箱子。
说实话,在三十岁以前我几乎没动过结婚的念头,我实在看不出那些
结了婚的女人和我比起来又能强到哪去,整天劳心劳肺不说,还要时刻提防
着免得让婚姻破产,像只惊弓之鸟似的。每当参加各种应酬的时候,我总是
那个能坚持到最后的女士,看到那些母亲。妻子们席间每每不停看表,接连
道歉着提前退席时,我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一一我毫无后顾之忧。
然而自从我奶去世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和无助。
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去,开了院门进去之后,便立即反锁上,再开了屋
门进去之后,接着又反锁上,然后就一个人在里边或蒙头大睡,或彻夜看电
视。
或干脆就无聊地在两个屋子以及厨房之间晃来晃去。所以一般只要有
人请吃饭,我是逢请必到,从不推托,反正回家更没意思。好在于我们这行
被请的机会很多,我家里的锅灶几乎很少派上用场,一袋大米吃一年。
“你恋爱过吗?”趁朱姐给我添茶的空隙我赶忙插了一句,问了一个最
关键的问题。
没有,从来没有。不怕你们笑话,我在单位人缘儿不好,工作以外几
乎不跟任何人来往,从来没有同事去过我们家,我也从不去别人家。考大学
时我也是报的哈尔滨的学校,这样回家方便,可以走读。所以那时我跟同学
们也比较生疏,上课才来,下课就走,一向独来独往,从未想过,也没有机
会去恋爱。等到真想爱一把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无人可爱,年龄、层次都相仿
的早已是别人的丈夫,年龄合适的往往又层次太低。有人甚至给我介绍过一
个开肉铺的个体户,我一听就火了:“这不是糟贱我吗,我又不是为了结婚
才结婚!”那通火发过之后,从此再没有人提给我介绍对象的事了。
所以我一来北京你就那么当回事儿似的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忙碌,
令我一直很感激。我这个人很自私,也很要强,多年来从来不愿开口求人,
但也从来不会热情地去帮别人,当然也就体会不到实心实意被别人帮助的幸
福,你是第一个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人,老何是第二个。”
我不由坐直了身子,再看朋友也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放下了饭盒。
老何是我来北京以后接的第一个案子的当事人。我们现在这个事务所
规模很小,连主任在内只有四名律师,案源又少,所以杂七杂八的案子都接,
老何这个官司很简单,就是和老婆离婚,财产分配上扯不清了,所以找到我
们所来咨询,正好是我接待的,从此我们俩也扯不清了。
后来老何这场纠纷是我兔费为他代理,帮他划上句号的,不过他也没
占到什么便宜,房子最终判给了女方,因为当时是女方单位集资建的楼,虽
然按判决女方应该在经济上有所补偿,但老何一分钱也没要,从那个家出来
时除了衣服和书什么都没拿,甚至比当年结婚之前还要穷,他说虽然老婆不
再是自己的老婆了,可女儿却永远还是自己的女儿,他希望被判给母亲的女
儿今后的日子能好过些。
他有一个今年已经七岁的女儿。
老何其实并不老,三十五岁,比我大一岁,但他长的老,加上平时说
![[综英美]从阿斯嘉德到221b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2113.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