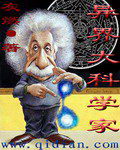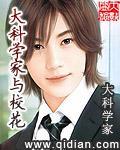哲学科学常识-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离开原来的现象越远,越不大可能被期待,我们就会越说这个理论或模型良好。这就意味着它们不只是发现了规律,而是发现了机制。那种专门发明出来对付眼前事例的理论〔ad hoc theory〕是无趣的理论,缘故在此。库恩所说的理论丰饶性,是从表观上说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它理解为这一理论进入了深层机制。麦克姆林说,丰饶性这一标准减少了ad hoc理论、一事一说法的理论的可能性。
科学所欲把握的深层机制是远离日常经验的机制。我们只有通过理论的、推理的方式才能到达那里。近代物理学通过数学化获得了这种远行的能力。我在前两章表明,量的纯外部关系保证了长程推理的可靠性。正是这种长程推理的可靠性使得科学可以发现或建构远离经验的深层机制。科学做出预言的能力是以数学化的方式达到的。从英文词calculable来看,量化和预测差不多是一回事。但这不是说,只要我们量化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量化和预测是通过机制联系在一起的:量化保证了长程推理的可靠性,长程推理使我们能够掌握远离经验的机制,掌握这一机制使我们能够预测。
科学做出的预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预测。人们说,科学提供精确的预测。由于我们被“精确”这个词的褒扬意义迷住了眼睛,反倒忽略了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先行数量化。科学理论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够做出更准确的预言,它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做出准确的预言,这些事情和我们平常做预言的事情不同类。爱因斯坦理论对行星的实际轨迹做出的预测比牛顿理论所做出的预测更精准,这里的“更”是在两个科学理论之间的比较,至于我们普通人,不是我们的预测不够准确,我们在这里根本无从预测,最多是臆测。反过来,我们预料张三会升官,李四会发财,在这些事情上,科学并不能提供预测,遑论更加精确。科学理论的本领是在我们平常根本无法做出预言的地方做出预言。科学的极高的预测能力,说来说去是预测能够量化的东西:纯量的活动,或者能归化为纯量的活动。而我们的经验世界,原则上是无法大规模量化的。
科学理论不是直接来自经验,它以外在于资料的假说形式出现。这些假说,通常是由通过远程推理得到的一些结论建构起来的,这个推理过程往往牵涉理想化的前提和条件,往往或明或暗地引入了一些尚未证实的东西。这些结论建构起来的假说是否正确有待于验证。假说…预测…检验…理论的程序是和实证理论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是在实证科学兴起之后,假说才被用来指称理论,预测才对判定理论真伪起到决定作用。Savoir pour prevoir〔知的目的是预知〕这话出自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之口,不亦宜乎?
预测与假说(6)
如上所言,科学理论不是预言已经发生过的现象还会重复发生,它根据机制预言新颖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理论能够做出这一类预测,才使得验证成为可能。这类新颖的现象可能从没有被经验到,甚至从不可能被经验到。要验证现代科学理论,经验不够了,直接观察也不够了,理论需要通过实验所生产的事实来加以验证。不是“验之于经验”,而是验之于实验。科学预测和实验是紧密关联的。我们曾强调经验与实验的根本区别。相应地,我们在这里要强调验之于经验和通过实验来证明有根本区别。其中的一个区别是,经验是自然的、回溯的,所谓验之于经验所需要的是判断力。这和依据一个假说设计若干实验来加以证实大不相同。
无论阴阳五行理论还是各种哲学理论都不能发现可经验范围之外的规律,也不能掌握可经验范围之外的机制。阴阳五行理论若被理解为关于机制的学说,那么,我们可以基于其预测的失败把它视作伪科学。哲学呢?哲学也常被视作或自视为发现规律和发现机制的学说。结果,那些热衷于总结规律、发掘机制的哲学爱好者,要是没有成为科学家,就会成为最无聊的“理论家”。但如下一章所要辨明的,这种冲动出于对哲学的误解,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哲学研究的鹄的并不在于总结规律,发掘机制。哲学是对经验的反省,尤其是对概念的考察。哲学理论是要让世界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可以预言。只不过,概念考察和机制研究、尤其是定性的机制研究,有多重交织,极容易被混淆。理解有举一反三之功。哲学扩大其“适用范围”的方式和科学理论是不一样的,哲学引领我们在深处贯通,在这里,理解的深度意味着理解范围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这和科学不断推进以把握深层机制从而扩大了应用范围是可类比的,并因此容易引起混淆。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στυφχψωστυφχψωστυφχψω
在日常生活中,对事态做出较优预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事态的较深理解。依此类比,我们会设想,科学理论既然能做出更准确的预言,表明科学对世界有更深的理解。但如上文所示,科学的预测能力涉及的是某些特定的事情,可以也必须通过量化才能把握的事情。由此,科学具有预测能力并不一般地表明科学对世界具有更好的理解,除非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一些我们日常经验没有想到要去理解的并且也无法理解的事情上,科学提供了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和通常理解有别,本书称之为“技术性理解”。在技术性理解的意义上,科学理论做出预言的能力当然依赖于理解。
但如“万有引力与可理解性”、“为什么是数学”等节所提示,技术性理解并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科学理论可以做出良好的预测,但它对它所处理的课题并不理解。量子力学对量子事件的预测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但费曼仍说,没有人懂得量子力学。科学发现定律、做出预言的能力是以数学化的方式达到的,也是以数学化为代价达到的。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认为,现代科学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证明了它在一般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更好的理解。
所以,我们倒要反过来问:既然我们并不理解现代量子力学,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它呢?一位物理学家,B。格林,回答说:第一,量子力学在数学上是和谐的。第二,它做出的许多预言都得到了科学史上最精确最成功的证实。我们接受一个物理学理论的理由,和我们接受一个哲学理论的理由是根本不同的。
“我不杜撰假说”
牛顿有一句名言:“我不杜撰假说”。这句话引发了研究者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因为,如研究者早已指明,牛顿本人像所有科学家一样提出假说。
如上所言,“假说”有多种相互纠缠的含义。我们说牛顿本人也经常提出假说,指的是现在流行意义上的假说,――假说是需要加以验证的模式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牛顿当然提出假说。但牛顿说到假说,意思不同。牛顿认为:科学研究应当从现象中归纳出某种法则,然后再尝试把这些法则应用到更广泛的现象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检验这些法则是否正确。一开始对法则的尝试性表述,虽然尚未得到充分检验,但它并非假说,因为它本来就是从相当广泛的现象中归纳出来的。与此相对,杜撰假说是把单纯由逻辑构造或心智构造而成的东西当成某种实在的东西,赋予它们以实在。如果争论的一方只是从逻辑的可能性出发来否定通过归纳整理出来的法则,声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依赖于假说了。依赖于假说的争论将永无止境,因为总会有别种可能的。简言之,在牛顿那里,假说大体上指的是原则上无法通过数学方法和实验数据加以证明的理论。
现在通常所称的假说,当然不仅仅是逻辑上可能的,而且是材料最鲜明地指示的。上面说到,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做出了重要的预言,预言了三种未知元素的存在。但周期表本身是从62种已知元素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所称的假说…验证方法差不多就是牛顿所推荐的工作方法,标准的科学工作方法,和牛顿所反对的假说几乎正好相反。牛顿所称的假说,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思辨。就此而言,“我不杜撰假说”实际上是近代科学向形而上学发起根本挑战的宣言。
到十九世纪末,假说大量增加。这无非是说明,科学在观念上战胜了自然哲学,科学家再不会屈从于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的要求,都自觉采用归纳…假说…验证的工作方法。
一般的实在问题(1)
一般的实在问题
几乎没有哪本讨论物理学哲学的书不讨论物理学对象是否实在的问题。物理学是否提供关于实在的理论?是否在揭示世界的结构及其作用方式?实在论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们的立场又有很大区别。粗分,一些论者是防御性的,针对反实在论者坚持物理学理论的实在性。另有一些论者持物理主义还原论立场,主张只有物理学对象是实在的,惟有物理学才认识实在,常识所认识的世界不是实在世界。反实在论者的立场同样是形形色色。粗分,一大批论者从物理学理论的“操作性”出发否认物理学对象的实在性。另一批是所谓“强纲领”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主张科学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原论者可视作实在论中的极端派,社会建构主义可视作反实在论中的极端派。我们在导论里谈到过社会建构主义。关于还原论,我打算在另一种上下文中讨论。我所讨论的问题是物理学理论是否只是操作理论,抑或事关实在。本节中“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是在这一限定意义上使用的。
有些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把物理学理论视作约定、建构、操作理论,另一些努力证明物理学对象的实在性。前一个阵营被称作反科学实在论者,包括劳丹〔Larry Laudan〕、弗拉森〔Bas C。 van Fraassen〕等。库恩一般也列入这一阵营。后一个阵营被称作科学实在论者,包括亨佩尔、普特南、塞拉斯、Ernan Mcmullin等。
两个阵营的争论有时剑拔弩张。在一本题为Scientific Realism的论文集里,尽管大多数作者是或者至少自视为实在论者,鹰派反实在论者Arther Fine还是凿凿声称:“实在论死了。……的确,最近又出现了一些哲学文著,要支起实在论这个僵死的躯壳,给它吹入新的生命。但我相信这些努力到头来只能被视为并理解为哀悼过程的第一场,对死亡这一事实拒不承认的那一场。”争论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包括极为多端的议题,本节并不介入那些具体的争端,而是提供几个一般性的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搭建起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平台,从这个平台上瞭望,很多争论的端绪会变得更清楚一点儿。
反实在论者让我们注意,科学在不断改变面貌,从前得出的“科学结论”经常被否定。我们凭什么认为今天的科学结论恰恰就正确反映了客观实在呢?何况,我们不能轻易把这个不断否定的过程视作线性进步,不断地接近实在。很多人赞同库恩的主张,认为科学发展有时是革命性的,是不可共度的范式的转变,于是更谈不上不同科学理论的唯一客观基础了。例如,科学理论中很多看似指称性的名词其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