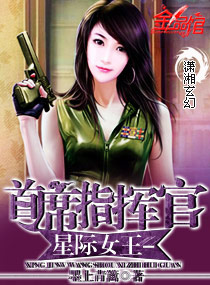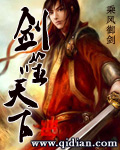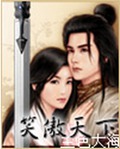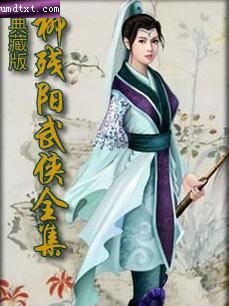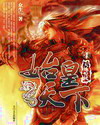天下残局-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深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後他也就破罐破摔,耍赖到底了——死前一日,他还下了两盘。
不过,曾国藩既成为谢安一样的中兴名臣,围棋于他的意义,就非只一项业馀爱好那么简单了。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曾文正公犹能从容镇定,每日不废围棋,早已成为美谈;他布置军事,常以棋理作譬,谙合兵法,更成为曾文正公一通百通、贤明睿智的明证。只是,经过文献统计,我们发现,上述美谈、明证俱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只是“主席什么都伟大”式的谀词。曾氏日记中,若某段时间频繁出现下围棋的记录,即可断定此时必为军事吃紧之时;闲暇较多之日,下棋的纪录反不多见。看来,棋之于曾,不过是killtime的心法,故此,他棋龄甚长,棋艺却极不高明。某人曾问吴汝纶:近日与曾帅对弈,感觉如何?吴连连摇头,答曰:臭棋篓子一个!我的棋也跟着变坏了。然则,曾氏如此臭棋,欲求乎大益于军事,似不可得。
因此,对谢安与曾国藩来说,围棋都不过是“矫情镇物”的道具。不幸的是,谢安穿了一双木屐,倘若如鄙人此刻足下踏一双塑料拖鞋,再怎么内心狂喜,都不致露出“屐齿之折”的破绽,更不必被後辈如房乔者阴阳怪气的说闲话。曾国藩则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一族,无齿折之虞,有藏拙之妙,故能将围棋的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成就一段美谈。
蒙汗药?拍花?汉奸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幸运的是,学徒昏然之状被村民发现,将他救下来,并将安三捉住,送到官府。安三自供“系天主教中人”,“惟问其迷药(来源),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教案发生後,涉案人王三供称:望海楼教堂谢神父(法国人,死于暴乱)向他提供迷药,他则“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被捉的安三,和武兰珍一样,也是王三“令其外出拐人”的“下线”。由此可见,洋教士支使本地无赖进行“迷拐”似非无因。
“拍花”案在清代并不稀见,即“拍花”所用迷药,其配方亦可考证。例如,“闹杨花、巴亚、蒙香、卤砂、山葛花、口口口”,即是配方之一种(为公共安全计,配药不宜全部列举,故用口口口代替其中某一成分)。清代刑部档案中有一件乾隆年间的“拍花”案(档案内“拍花”案件极多),与安三此案极为类似:河北文安人刘进喜,十三岁那年净了身,到庄亲王府内当太监,後因“打碎茶盅,心里害怕”,乃逃出王府,投奔别家作了佣人。一日,主人令其出外放驴,遇到一个道士,“他让我吃了一袋烟,我就迷了。他拉了我住店……我心里明白,又不能说话。他又给了我一袋烟吃,我越发迷了,他夜里就奸了我了。到第二日,将我的驴子卖了,我还糊涂,有当差人拿冷水给我吃,我才苏醒”。除了没被鸡奸,天津木匠店学徒被“拍”的遭遇和进喜一模一样。
作为勤于公务的地方长官,曾国藩稍加访查,便可对“拍花”一事了若指掌。但是,在天津教案的结案文件内,曾氏却说,教堂不但无“采生”、“折割”之事,且“无被拐情事”。要知道,除了王三的口供、安三的旧案,当日经他亲讯,业已知道“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按:仁慈堂是隶属教会的慈善机构。这些证据恰可用以令“洋人理曲”,他却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
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迷拐”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迷拐”、“折割”传闻嗤之以鼻:“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他的第一条“依据”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其次,他说:“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幽闭”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洗礼”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灵魂得救”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暴民”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福音事业”,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指标”负责。“指标”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慈善”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不肖”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