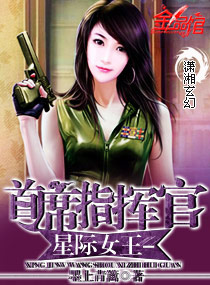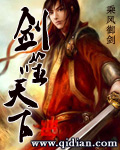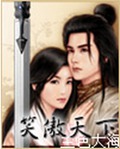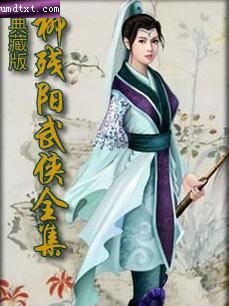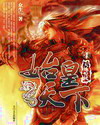天下残局-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古史辨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我们不是读书人”,而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略有接触”,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阶级”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後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作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迁变,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後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
大师兄是女孩子 谁家的女孩子
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今人多以此喻之发明权归诸胡适,其实不然,胡适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给他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而冯氏此“论”所据“底本”则是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段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民国八年)。由此可知,这个“女孩子”原名“实在”,俟经冯友兰从胡适身边抢去,则更名唤作“历史”。即今而言,其时之恩怨是非,早已化作烟云,不必一一析辨;惟“女孩子”此後之显晦荣辱、升降沉浮,则饶有趣味,值得一提。
“女孩子”一旦更名为“历史”,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金屋藏娇”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装扮涂抹”。自此以後(其实,此前亦然),“女孩子”便不只是单方面“千依百顺”的“服从”,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涂抹”她,她也要“装扮”你,适如玛丽娅?鲁宾逊所云:“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型,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更有意思的,则是试图对“女孩子”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价值观、时代性及影响力的差异,在如何“装扮涂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分化为不同群体,相互攻讦。适如柯文(PaulA。Cohen)所说:“文化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西方、传统性…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群体”用以相互“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的工具。柯文撰《历史三调》(1997年),则是对作为工具的义和团进行神话解构和历史重建的尝试。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经历”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来看,“事件”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事件”,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经历”与“神话”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幾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W。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义和”二字的英译、“九头蛇”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废立”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後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首倡“猎取拳民行动”——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後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後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