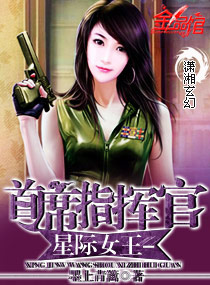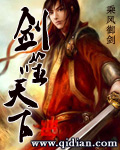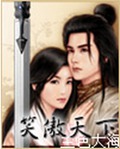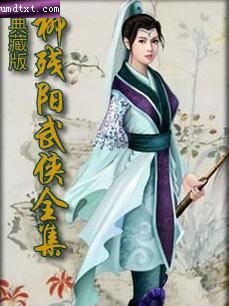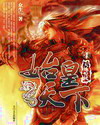天下残局-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塔齐布的辞典中,自无“人文关怀”一类词语,对翻云覆雨、今是昨非的“民族英雄”之定义亦当不甚了了。他怀抱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只知道“忠心报国”(他的左臂刻此四字)之馀,儿童少年多属无辜,即使敌人也不应滥杀(且可施救)。此种情怀,或可称为“慈悲”;太平军中亦有一位名将,与塔齐布同此慈悲,斯人即忠王李秀成。
咸丰十年春,李秀成率军击溃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为死不挪窝的洪秀全第六次解除了“京围”。江南大营统帅张国樑,“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此役战死于乱军之中,尸骨都无觅处;亏了李秀成,在丹阳南门护城河里找到他的尸体,以礼葬之,一代名将才入土为安。李秀成回忆此事,说:“两囯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是恤英雄之心”。
嗣後,李秀成攻克苏州和常州。入城後,“苏民蛮恶,不服抚恤”,镇日在城内搞“恐怖行动”。部将怕局面失控,建议屠城,秀成不许,毅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安抚居民。他亲率数只小艇,深入乡镇,苦口婆心劝民众放弃无谓的抵抗。乡民却手执器械,将他围住,“随往文武人人失色”,秀成已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故不许下属动手,只是继续劝解。终于以诚动人,“各方息手,将器械收”。用这个办法,七天之内,“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以故,苏、常虽被战火,百姓却免遭荼毒。
其後,秀成挥师围杭州。总攻之前,他便开展思想工作:不分军民,不论满汉,“肯降者即可”不杀。前此,太平军于克城後,对“满妖”甚为仇恨,杀戮甚于汉人;这次,为了“和平解放”,秀成特向洪秀全申请投降满人亦得免死的“御照”。御照批准,自南京颁至杭州,需二十馀日;御照尚在途中,秀成已攻入杭州,他为遵守诺言,特令暂停对内城——满人皆居于此——的攻击。杭州将军瑞昌,是当日在杭满人的首领,却不信“髪妖”的承诺,拒不投降,且乘太平军停攻,遣洋枪队偷袭军营,打死一千多人。秀成无奈,只得进攻。满洲兵本无战斗力,一击即溃,瑞昌自焚死,连带其他满洲人,亦大半死伤。秀成入城後,亦未因满人顽抗而屠城,且以德报怨,将瑞昌的一副焦骨棺殓妥葬。他并发布公告,安抚城众,云:“尔逢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丰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之意。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为止”。秀成之攻占,有礼有利有节,不仅不滥杀,且准许老百姓自定去留,欲走而无旅费者,甚而提供资助。以愚所见,咸、同间战争持续约二十年,交战双方数十支军队,惟有秀成之军,真不愧为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躲不开的炮弹
湘军最终成功,水师功不可没。水师作战,除了注意风向和江水流向,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防御炮火。攻击船只的炮火来源有二,一是敌方船舰,一是江岸炮台。每当进攻江面要塞,水师船只便须应付来自前方和左右两侧的炮火,如何防御这种“交叉火力”,是水师统帅彭玉麟久思不得其解的大难题。湘军的营制、阵法大都脱胎于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彭玉麟也到这部书里找答案。戚氏书中提供了两件宝贝,一个叫做“罟网”,即用十幾层渔网悬挂于舰船左右两面,以备轻度炮火;一个叫做“刚柔牌”,以湖棉和头髪搓揉成团,压成板状,外蒙漆牛皮。彭玉麟依法制作,并实战演习,结果令人沮丧:“炮子一过即穿”。国防科技日新月异,西式重炮大量流入中国,老办法行不通了。
技术引进不可行,只有自行研制。在彭玉麟的亲自指导下,湘军科研人员作了大量试验:打湿的棉被;生牛皮加藤牌;用编竹、牛皮、湿棉被、头髪压缩成盾牌;等等。花样百出,结果依然是“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当时,大炼钢铁的洋务运动尚未展开,从技术上来说,彭玉麟已经山穷水尽。可是,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关卡一日不破,湘军恢复东南的理想就一日不能实现,怎么办呢?只好硬上。彭玉麟与水师将领闭门开会,想出这么一招:弃用各种舰船防护措施,“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
湖口一战,就采用了这种“新战法”。据载,当日彭玉麟亲率水师幾百艘艇列阵冲锋,众将士遵令“植立船头”,其时,太平军船炮、岸炮齐发,湘军水勇“出其矫捷之身手,与敏锐之眼光”,能躲则躲,不可躲则成仁,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太平军一看傻了眼,赶紧疯狂发炮,无奈那时的炮火攻击有其局限,霰弹不多,频率不快,并不能真正织成一张无法逾越的交叉火力网;因此,湘军死伤虽众,到底还是有百十艘突破防线,杀到太平军水师跟前。两军水师面对面交战,湘军的装备、经验极具优势,故一举击溃太平军,夺下湖口。
自今日看来,这种战法太过残忍,缺少人文关怀。但是,不这么干,湘军就控制不了长江;控制不了长江,就围不住南京;围不住南京,历史就得改写。过程与结果,何者更重要,历来是两难之局;彭玉麟斯人已矣,这些思考都留给後人,後人找得到正解么?
报应
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原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麾下猛将,咸丰十年,被派往安庆帮助叶芸来守城。他受命在城墙外修筑堡垒,充当第一道防线。当日攻城者是曾国荃、曾贞幹两兄弟,枪炮地道各种战法,轮番猛攻,深处最前线的学启实在有点吃不消;兼之他与叶芸来的关系不咋的,每日孤悬城外,军火粮草各类接应也时常失误,憋了一肚子气。内气不顺,外压严重,这人的心思就不太好掌握,果然,明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他便率领一干人马,跳槽到了湘军。不过,降人历来难做,曾氏兄弟对他只是半疑半信,并不敢托付太多。湘军当日在安庆城外挖了一道长濠,曾国荃命令学启带队驻扎在城、濠之间,湘军大部则在濠外驻扎,声言没有统帅手令,学启不得退扎濠外。湘军这边且备炮数门,瞄准学启之部,一旦违令後退,就炸他个血肉横飞。隔在太平军和湘军之间的程学启,恰如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
一番血战後,安庆告破,学启挺过了这段艰难岁月。但是,不被信任的阴影并未与硝烟俱散,因此,李鸿章受命赴援江苏并创立淮军,学启毫不犹豫选择了跟这位安徽老乡去闯天下,对湘军并无半点留恋。抵苏一年内,学启率开字营一千人进攻退守、所向克捷,并成功整合西洋(戈登常胜军)与本土(淮军)资源,摸索出一套土洋结合的犀利战法,打得太平军节节败退。同治二年秋,他与戈登联手围攻苏州,水陆并用,长(西洋炮)短(单兵搏杀)结合,步步逼近。城内士气低迷,便隐然有了和平解放的意思,经过秘密谈判,以郜云官为首一干不肖将领谋杀了主帅,献城投降。故事讲到这,若能戛然而止,未尝不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局面,哪晓得受降当日,学启却将降将们杀个干干净净,不仅引发一场外交风波,且埋下“杀降不祥”的伏笔。英国人戈登是这次交易的保人,闻知降将尽诛,勃然大怒,拎着手枪便要与鸿章决斗,与学启“开仗”。在沪西方舆论也是骂声一片,并闹到北京总署,称须严惩涉案人员。幸亏鸿章是洋务先锋、公关高手,立即启动危机公关,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是,对学启来说,却逃不掉,次年三月,他在一次战役中头部中炮,脑浆迸裂而死。
据说,汉代名将李广因为杀降,终身不得封侯。学启则以降人之身杀降人,情节更为恶劣,中炮而死也算是不爽吧。
少年杀人事件
在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电影《冷山》中,与英雄(裘德?洛)美人(妮科?基曼)为敌的一伙人,叫做民兵(HomeGuard)。美国南方“叛军”于战时设立民兵组织的初衷,乃是希望民兵协助正规军队保卫乡土,兼且维护战争时期的地方治安。然而,大多数民兵的实际作为,却如影片所述:鱼肉乡民,掳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比敌军还可怕、可恨。咸丰、同治间,各省为抵抗太平军和捻军,也组织了许多类似的团体,一般称为“团练”,其上者固能不辱使命,甚且超水平发挥,一变而为正规军,如湘军和淮军。其不肖者则与美国民兵隔海呼应,地痞恶绅们纷纷出动,充任团总、练总,带领一帮乡里“莠民”,欺压良顺,无恶不作,刘铭传家乡安徽肥西一带的团练,就是这种“劣团”的典型。
某日,当地团总传唤铭传之父刘惠到团部,踞坐马上,责问老汉近期“军需供应”工作为何屡屡延误。刘家世代都是普通农户,自开办乡团後,家中钱谷已被折腾一空,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供办;老汉据实禀告,并请求捐免。团总大怒,扬鞭立马,当众将老汉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严厉警告:若再延误,老不死的你可得小心着你的老命。老汉回家,且羞且惧,全家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适逢铭传自外归来,了解状况後,振臂而起,对众人说了句:我还不信就没天道王法了,我要跟他死磕!话音未落,十八岁的铭传已经纵身出门,直奔团部所在地,要找那无良团总单挑。
小伙子怒冲冲找到团总,下了战书。团总仰天大笑:哈哈哈,你小子有种!来来来,我的佩刀给你,真有种你就砍了我罢。团总身边,练勇簇拥,剑戟森严,他料想这个少年慑于形势,必然不敢接刀;孰知铭传眼明手快,不转瞬间,已握刀在手,再一转瞬,则刀起头落。随後,左手提着首级,右手挥动钢刀,铭传跃身上马,面对呆若木鸡的观众发表演讲:某团总为害乡里,兄弟我已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从今往後,就由兄弟我带领大伙儿办团练,愿意跟我干的站左边,不愿意的站右边,啥也不干的站中间。演讲毕,全场肃然。幾分钟後,掌声雷动,数百人争先恐後站到左边。自此,不管是抵抗太平军、捻军,还是与其他民团进行械斗,铭传率领的这支民间武装都能所向克捷,成为安徽境内知名的劲旅。後来,铭传带着这支队伍投奔李鸿章,更成为淮军中的第一王牌军。
七年後,铭传投到李鸿章麾下,南征北伐,战功赫赫,其所统领的“铭军”,遂成为淮军乃至天下的第一劲旅。
含冤的铜盘
同治三年初夏,刘铭传攻克常州。入城後,生擒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磔”(肢解)之,并入驻护王府。一日夜深,铭传未睡,闻得窗外丁当有声,如剑佩相击,乃掏出手枪,出外察看。下到庭院,除亲兵拥枪肃立外,别无人迹,而丁当之声不绝,不觉纳闷。循声追踪,发现丁当之声来自马槽,近前一瞧,却是马儿吃草,笼头铁环和槽沿碰撞发出声音。铭传心细,知道铁环、石槽相碰,发声不应如此清脆,其中定有蹊跷。便仔细观察这具马槽:其色,则黝黑污秽;以手叩槽,其声却“清越以幽”,如作铜鸣。铭传大奇,嘱咐亲兵将马槽擦洗干净,明日抬来见本大帅。
这具“马槽”,公元前815年铸成,学名为“虢季子白盘”,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