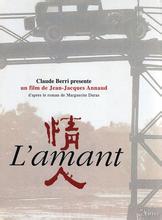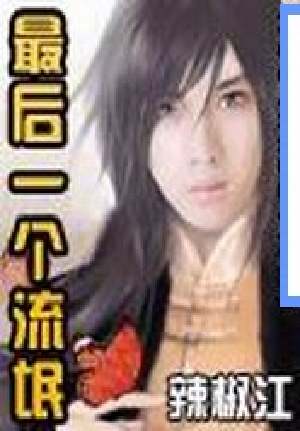最后一场人鬼之战-第8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我根本没有听到枪声,但一颗子弹打中了我。
我正想跟着依诺船长身后钻进教堂,右锁骨的上方突然像中了一枝冰箭。这一箭将我射了个对穿,从右后背穿了出去。寒意头骨彻心,相比之下,教堂周围缭绕的寒冷雾气简直像亚热带的暖风。
我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在我晕倒之前,我看到依诺船长折了回来,冲向我,船长单膝跪倒在我身边,惊呼道:“葛里菲兹,快和我把他搬出去,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中弹了,是哪个杂种开枪打伤了你?”
显然,依诺船长也没有听到枪声。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中弹了。我想:哦,对了,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中了枪弹,不是什么冰箭。
接下来,我发现自己躺在教堂门前积雪的砖地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到了这里。这种感觉很像打了一个盹,醒来后一时恍恍惚惚的。但身体着地处的疼痛表明,我刚才狠狠地一头摔倒在教堂正门里的大理石砖地上。
我仰面朝天,看见了依诺船长正站在我身旁。
接着,我透过自己脑袋上方的那些薄雾,发现了教堂正门上用花岗石嵌出的铭文:
他引领我们升入天堂。
他奶奶的,升你个头,到底是哪个混蛋嘣了我一枪。
我在心里暗暗咒骂了起来。
“孙,你别使劲,我们刚刚才帮你止住血。”依诺船长握着枪,背对着我说道。
“是谁?是谁干的?”我大声嚷道。
“还不知道,你一中枪,我们就赶忙把你抬出来了。葛里菲兹回诺亚方舟拿疗伤、消毒的药还有绷带了,你再忍忍。”
就在依诺船长说完这句话的转瞬之间,冰箭透体而过处从奇寒变成了火热。伴着高热而来的是撕裂般的剧痛,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是我第一次被子弹打中,先前我脑中枪伤的抽象概念终于靠疼痛转化成了现实。
剧痛之中,我还是听见了远处几个人跑步赶来的脚步声。
我知道,是葛里菲兹从诺亚方舟上拿到了应急药物赶回来了。
一同赶来的还有雅格布上校、罗宾上尉和三名美国士兵,葛里菲兹解开了事先缠在我肩膀上的衬衣。
我看到了葛里菲兹从拉普达生物研究所里带出来的那只鱼缸大小装有小半盆培养液的培养盆,他正小心的用棉花棒浸着那些ru白色的菌种,然后均匀地涂抹在我的伤口上。
我问道:“这是什么?”
葛里菲兹埋着头,说道:“疗伤菌。”
我感到伤口处的疼痛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有些不明白,继续问他:“疗伤菌?疗伤菌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儿好像挺管用的!我的伤口好多了。”
“嗯。”葛里菲兹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道,“这是当然的。这东西德国科学家以前发现的,是一些无脊椎动物用来抵抗天敌和进行自行疗伤的一些特殊的聚酮类化合物,但是并非由它们自身分泌的,与其这些动物共栖的低等细菌才是它们自行疗伤的药物,也就是我现在给你擦拭的这种白色菌类化合物。”
“我想起来了。”我说道,“那些丛林里的猫科动物,只要一受伤,就会死命地跑到一个大泥坑里躺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些泥坑里,我想应该就有你刚才说的这种白色菌类吧?”
“没错,这和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不过我给你用的这些,是空岛人提纯后的化合物,比泥坑的效果要好得多。”
我奇道:“空岛上怎么会有菌类化合物,那上面的土地不都是云壤吗?”
“他们是从昆虫里得到的。”
“昆虫?”
“是的。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生物研究所对空岛上的隐翅目甲虫进行了基因研究,通过对甲虫及其共生细菌的基因分析,他们发现甲虫用来抵抗诸如蜘蛛等天敌的聚酮类物质都不是甲虫自身分泌的,而是由一种与其共栖的低等细菌生成的。这些和我们陆地上的低等细菌是同一种东西,空岛人跟踪隐翅目甲虫,找到他们的巢穴,就会发现大量这种低等细菌的混合物,然后加以提纯,就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治疗药物了。”
“原来如此。”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我感觉那些白色菌类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身体内的疼痛彻底消失了。
只是,我的右肩膀与右手臂还暂时不能活动。
不过,我相信自己会马上恢复起来。
第046章 教堂惊魂 (下)
伤口用厚实的绷带扎紧了,不用担心出血。
我这时候才发现,葛里菲兹还有罗宾上尉手上都拿着军用霰弹枪,这是美国对越南战争时曾使用的“雷明顿(remington)870”泵动霰弹枪的改进型号,射程比老的型号增加了一倍多,由于改进型雷明顿霰弹枪的射程在200米左右,所以减少了一些因跳弹或贯穿前一目标后伤及后面目标的概率。
葛里菲兹看到我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下来,才站起身来,举起霰弹枪,对依诺船长说道:“进去吧!”
依诺船长道:“你先等等。”
他转过身来,对着教堂敞开着的正门,大喊道:“不管你们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打伤了一个我们的同伴。如果你们还不打算现身的话,我们就不会客气了!”
依诺船长说完之后,也举起了手中的左轮,枪口对着教堂正门。
良久,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在我们都以为里面的混蛋不打算妥协的时候,大家听到了两声枪响。真响啊,一点儿也不像那颗无声无息将我击倒在地的子弹。但这回我们之中没有人倒下,因为,这两枪是朝天空开的。
这是示威吗?或只是表示教堂里的人并不好惹,你们想进来就试试?
我不知教堂里面那些人的意思,我的同伴们同样不知道。
大伙们用离子手电筒向正门里照去,想瞧瞧我们那个有些神经质的敌人究竟离教堂正门有多远。
从刚才的两声枪响来看,敌人离这里的距离并不远。
我站起身来,望着里面,我看到教堂里的其中一个身影已经朝我们所有人直奔过来,只有几码远,对霰弹枪毫不在乎。
可另外一个离正门还挺远,远在霰弹枪的射程之外。在离子手电的白光中,教堂的大理石地面被照的雪白雪白的,在这雪白的地面尽端,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在运处黯淡的手电光中看不清这个身影的脸。
那个向我们奔过来的身影,在离我们六十米左右的距离,突然改变了运动方式,他在教堂大厅的长椅中来回穿梭,前后奔突,瘦瘦的身影迅捷无比,就算身躯全部暴露在离子手电的光线,我们竟也没能看清他的模样。
不过,我们能感觉到杀气,像冰一样的杀气,像打穿我们右肩膀的那颗子弹一样冰冷。
我虽然看不清楚,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正盯着我们,像一头盯着羊群的狼,耐和性子,将我们的一切动作看在眼里,耐心等待着我们这群人暴露出弱点的最后时刻。
我头这时候有点晕,可能是先前失血过多的原因。
罗宾上尉看我又要晕倒在地,赶忙把霰弹枪背在背上,过来把我扶住。
“还撑得住吗?孙?”罗宾上尉有些心惊胆战地问道。
“还死不了。大家……大家先别进去,里面的‘东西’动作好快,别等着让他再给我们来一枪。”
葛里菲兹道:“我也觉得这样最好,大家先回诺亚方舟,从长计议。”
失血过多的我,好像反倒让我的头脑清醒了。“大家慢慢后退,如果那东西不过来,就别lang费银弹,等那东西走近再开枪。先把我扶回诺亚方舟,我现在是个累赘。”
……
其实,我现在心里很是不爽,无缘无故的被人嘣了一子弹。
还好没打在心脏附近,不然的话,我今天搞不好就命丧此地了。
大风大lang都挺过来了,在阴沟里翻船,那可划不来。
回诺亚方舟等我恢复了体力,看我不把教堂里的那些小杂种都给宰了。
管那些动作迅捷的东西是些什么生物,反正大家都已经肯定不是人类了。
回到诺亚方舟后,我在葛里菲兹的手中看到了打穿我又肩膀的那颗子弹,看到子弹,我才了解到什么是心有余悸的感觉。
听葛里菲兹说,幸亏这枚子弹的口径很小,如果是大口径子弹的话,比如说普通的一颗7。62mm口径的步枪子弹以850米/秒的速度射穿人体之后。
首先,它会在正面射入点皮肤上留下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口,而弹头在经过身体时形成的巨大力量会震伤脏器。
然后,以570米/秒的速度穿出人体,震波形成的出弹伤口直径有可能达到12厘米以上!
如果是打在头上,创口将更为可怕,它将掀飞你三分之一的头盖骨。
当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f。kennedy)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殉国的,在现场录影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弹头恰好击穿了动脉,在心脏泵血83。3毫升/秒的强大压力下,血液可以喷射到10米以外的地方。
如果是在房间里,清理现场则变得很麻烦,要洗净墙壁、家具和天花板上所有的血迹和被弹头带出的一些脏器残渣。
在中弹倒地时,人体中约有4000毫升血液。在其后短短的几秒钟里,出血量很快达到1000毫升。
一个几秒钟前还活蹦乱跳、充满思想的人,就会立即濒临死亡!
这个数据还只是指女性。
如果是男性,只要400毫升就够了。
这个概念是通过化学实验室里的量筒得知的。
而从视觉上,你感到恐惧。
除去大量的血迹,你还将看到从创口渗流出的体液,溢出的内脏和外翻的黄色皮下脂肪。
在德国,有许多二战老兵战后都回忆,被子弹击中后感觉真的很糟糕。
参加过市场花园战役的一位德国空降兵,曾详细地说过自己的感受。
那天,他们被安排增援被困的德国部队,他一下卡车后,就被从侧方跑来的一个拿着汤普森突击步枪的美军击中小腿。
顿时,他看见自己小腿上的骨头和皮飞了出来,他清楚的看见地上有自己一小片腿骨,还有一颗子弹打掉了他半片耳朵,他回忆到当时真的是刻骨铭心的疼痛,简直是下了地狱,被子弹击中的头几秒会感觉到冰冷的麻木,但后来却是像有千百万根针刺向你。
这个德国士兵的感觉和我的感觉是相同的,我想他感觉到的千万根针应该是千万根被烧红、发烫的铁针才对。
如果不是子弹的口径较小,如果不是那天空之城中神奇的、经过提纯后的疗伤菌培养液,如果打中的是身体要害部位。
那一枪就会直接要了我的性命。
……
可恶!
第047章 傀儡士兵 (上)
生命的本质是机体内同化、异化过程这一对矛盾的不断运动,而死亡则是这一对矛盾的终止。
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神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到最多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问答。对此,我觉得很难以理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的音乐。
不知道身为基督教徒的爱因斯坦先生,如果被住在基督教堂里的恶徒用子弹打穿肩膀,还会不会有这么的坦然。
在稳定、和平的人类社会走向黑暗时代的关口上有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个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但现在教堂里的这群‘东西’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大概闭目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