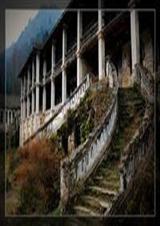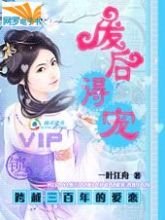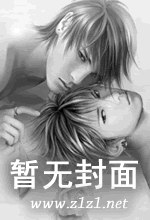百年功罪-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包括毛泽东的名言,政治术语,特殊名词、口号、缩略语,民谣民谚,京剧和电影对白等等,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着,被作家写进小说和剧本,被老百姓极其鲜活地挂在嘴上,有些还被赋予新的内涵,或依其形式创造、组合出新的词语。一些人把它们统称为“毛氏话语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文物的“活化石”。
从图书馆、档案馆里,可以找到当年正式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图片,如果找找关系,还可以查到某年某月印发至某一级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官方文件,对于我们领略历史可以被粉饰打扮成一副什么模样或许有好处,但不能让我们领略历史本身。谁都知道,历史是最经受不起粉饰打扮的。
在一个言论出版受到严密控制、高度极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被称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形态里,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大量发表而又不需经官方审批、不代表官方意愿的文字吗?
有,那就是大字报。
二、
第一张大字报起于何时,大概是很难考证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举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说是大字报。然而,赋予大字报以特定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流行于世界的专用名词,却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也不论我们是带着感情色彩还是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作为“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有专门政治含义的大字报,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认为“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求实行“大鸣大放”。毛泽东当即肯定这一要求:“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辩论、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法,简称“四大”。文化革命不过是将这“四大”推向极端和高潮罢了。
仔细说来,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和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才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形式。鸣放和辩论,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笔;用嘴叫“口诛”,用笔叫“笔伐”。即使不说中国是一个重文本传统的国家,仅从口舌与笔墨二者的份量来比较,后者也明显更具有空间堆积和时间持续上的优势。常言道:“口说无凭”,只有“笔写纸载”才不容忽视和抵赖。从大批判的实用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口舌转化为笔墨较难,笔墨转化为口舌较易(照本宣科即可),还可以无限反复地转抄、翻印、宣读和散发,在录音设备还只是少数新闻单位的专业器材的当年,“笔”的威力和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嘴”。因而实际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九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显然,宪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报这“一大”。鸣放和辩论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活动,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邻舍对骂,小俩口拌嘴,文坛上打笔仗,学术界的商榷,会议上的争执,法庭上的指控和辩护,议会的议案,选举时的论政,党派内外的矛盾,政治、军事和经济谈判,民事纠纷的调解,……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都可以统称为鸣放或辩论,由任何宪法来规定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重其事地特别予以规定为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么,什么是大字报,我们怎样来定义它呢?最简单最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大字写成并公开张贴的文字。查王同亿主编的《汉语大典》:
大字报〔bigcharacterposter〕发表意见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写成贴出,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时颇为流行,后被取缔
辞典的条目解释,与最简单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种解释太不完全太不确切了,作为一种“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作为词条的解释简直就是错误。所有的商业广告词都是“发表意见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写成贴出”,──如“挡不住的诱惑”、“它使我恢复青春”、“四季如春的感觉”、“『咳』不容缓”、“不打不相识”……。另外,现在仍流行使用的标语、横幅、海报、告示通知、感谢信、祝贺信、道歉信和检讨等等,也都符合该条目的规定。如果它们都可以算作广义的大字报,那么又不符合“后被取缔”的说法。
反过来,大字报也并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说用“大字写成”了。文革期间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大字报是漫画。还不要说,这些漫画的艺术造诣,往往远胜过文字稿的文学水平;即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也绝不能略过不提。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宣布:“街道是我们的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在苏联这只不过是一种宣言;而付诸行动,只能在文革时的中国。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没有漫画的大字报和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当然,还包括大批判专栏刊头报尾的宣传画。有人甚至认为,由这些漫画、宣传画组成的文革美术,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唯一能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某种地位的中国美术。
这样认为可能偏颇,却说明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重要到了怎样的地步。当然,如果略作改动,把词条解释中“发表意见的文字”改为“发表政见和民意的文字、图画”,也就比较接近我们所讨论的大字报了。
四、
大字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大”。
它可以把任何弱小的声音,不论是鸣放还是辩论,是发表政见还是传达民意,是指责、攻讦、控诉、揭发、质问还是辩解、反驳,是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都可以通通放大为大声呼唤。
由于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愿意不愿意看,它都要直钻你的耳膜,直闯你的眼帘,直扑你的脑海,这就是所谓“打入性”。
由于大,你想躲躲不了,想逃逃不掉,它可以贴到你的办公桌上,贴到你的门口,贴到你的床头,贴上你的锅台旁、茅坑边,直至贴到你的身上,如影随形,无孔不入,这就是所谓“侵犯性”。
由于大,铺天盖地,呼风唤雨,摧枯拉朽,震聋发聩,“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使你感觉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仿佛将立刻陷入灭顶之灾,这就是所谓“威慑性”。
由于大,你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缺陷、隐私,你干过的坏事、丑事、憾事说过的悄悄话、私房话、甜言蜜语、怨天尤人、东家长西家短,总之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兜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众人围观、欣赏、品评、嘲笑,这就是所谓“公开性”。
由于大,它的每句话每个字都饱蘸浓墨,气势逼人,一笔一划如同投枪匕首,乾柴烈火,看得被批判者第一眼头晕目眩,第二眼血往上涌,第三眼手脚冰凉;修养好的也免不了加快呼吸和心跳,乍出一背细密的冷汗。这就是所谓“战斗性”。
由于大,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大而概之,无须仔细推敲,以断章取意来省简笔墨,以望文生意来代替严密论证,以上纲上线来加强效果,既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可以反戈一击重起炉灶,这就是所谓“粗率性埂
由于大,它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尤为深刻,即使你一目十行,也可以过目不忘。如果这张大字报是针对你,或你的家人、亲友、同事、邻居、仇人的,那就更让人耿耿于怀、永志难忘了。这就是所谓“持久性”。
五、
这一“大”的形式特点,使我们今天的重读大字报成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是不可复制的。纵使找到那些堆埋在故纸尘埃中的大字报文本,我们也不会再把它们用浓墨重新抄写,贴得到处都是,来身临其境地温习了。时过境迁,就算再造其境象拍电影一样搭一个场景,也无法追回早已流逝的那个时代。人事全非,而且绝大部份被批判者已经作古,这些文字放得再大,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神韵。弥衡击鼓骂曹,三国时令人动容和提心吊胆,于今谁要是再把曹操揪出来狠狠地骂个三五十天的,别人只会觉得好笑罢了。
一种文体,或一种艺术形式,总是以某个时代作为其存在的背景。背景消失,这种文体或形式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魅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在历史上流行过一阵子,后来也就不再流行了。其中,唐诗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然而也逃脱不了“至今已觉不新鲜”的命运。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人们多半只把它当成儿歌、口诀,教小孩子背诵,让他们显得聪明可爱,伶牙俐齿,总算是废物利用。
大字报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得那样迅猛,去得又那样突然;流行得那样轰轰烈烈,消退得又那样无声无息;给人的刺激那样强烈和深刻,过后却又找不到一丝痕迹。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文化运动象大字报那样,由那样多的人参加,制造出多得几乎无处不在的产品,然后消失得那样乾净和迅速
有人认为,这说明大字报文化的浅薄和不值一道,所以一把刷子一盆水,就把它冲刷乾净了,又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然而,还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和“值得一道的文化”,比大字报更吸引人的热情、触击人的灵魂、影响人的命运、暴露人的本性、改变人的观念乃至整个民族的语言、行为及性格特徵呢?
六、
大字报运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从宪法中取缔了关于它的条款。
严格地说,宪法只是取消了允许大字报的条款,并没有取缔大字报这一形式本身。那么,写大字报并不违反宪法。正如宪法没有一条规定允许人撒尿,但撒尿并不违反宪法。不过,在一般中国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传统习惯上,人的行为自由度应限制在法律、规章允许范围内,而不是扩大到法律、规章没有反对(不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能做规定可以做的事,而不能做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事。
当然可以理解成,宪法“不再保障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事实上,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保障,哪怕在这一形式的鼎盛时期。轻则围攻批斗,重则坐牢杀头,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有没有没吃过亏的例子?肯定会有的,但那也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