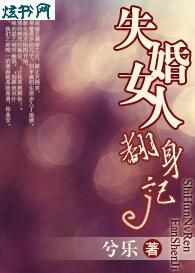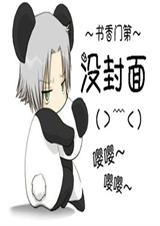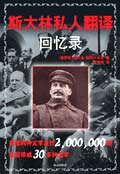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出现了一些人影,轮廓迅速清晰起来。这原来是斯特梯纽斯,以及与他谈话的英国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卡道冈。往隔墙上面一看,我在相连的房间看见了他们,并且他们所有的动作都重现在屏幕上。此前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电视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它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普通用品了。 从此往后,每次我来到美国时,经常与内森·洛克菲勒见面。 在纽约州州长任上时,内森常常请我到他的官邸。战后过了许多年,有一次,在一个明媚的夏日,饭后我跟他坐在他位于奥巴尼家中的阳台上,一起喝着卡布其诺酒,回忆过去的事情。我给他讲述了与我们在杜巴顿-伊科斯代表团有关的趣闻。当时,为了跟美国代表团的高级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将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罗基奥诺夫从“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这个故事,作为“各族人民领袖”古怪行为之一的见证逗乐了内森。 时间飞逝而去。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坏时好,但是我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会面,有时可以相隔几年,一直是稳定和得体的。 水门丑闻的结果,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下台。福特入主白宫,而内森·洛克菲勒则成了美国副总统。其时,我已经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主办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当了五年的主编。1974年秋到达华盛顿之后,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否跟从前一样给内森打电话,或者不必惊动美国副总统。我征求了多布雷宁大使的意见。他说我应该自行决定该怎么办,但表示相信,副总统找不出时间来见我。 最后我还是打了电话,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得知,内森·洛克菲勒当天下午三点在白宫旁边的独立宫见了我。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2)
就像以前多次一样,见面是无拘无束的。只是在一开始,有了一个正式的“照相程序”(这张跟美国副总统的照片稍后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给我)。此后,身穿海军陆战队礼服的侍者送上了茶点和一小杯烈性甜酒。 谈话像往常一样,从各自的身体状况开始,然后交换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新闻。难以避免地谈到了越战,那里美国人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失败。 “我应该告诉您的,”内森强调指出,“我们坚决打算撤出越南。但北越军队向西贡施加的压力,造成了我们撤退的困难。我们不打算就此事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我们也在极力争取避免采取强大回击的必要性,这样只会拖延战事。但是,由于早就认识您,”洛克菲勒强调说,“我想以私人的方式向莫斯科转告一个意愿,请转告你们河内的朋友们,让我们安排有秩序地撤出大使馆,以及我们的越南朋友,这样使我们能够适当地结束越南这段历史。” 我拿出“外交官”的分寸,对内森说,非常理解他的意思,但是,由于跟政府没有直接的联系,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们接着聊了一会,然后便告辞了…… 当然,就在当天,我的备忘录被用密电发往莫斯科。只是到现在仍不知道,洛克菲勒的呼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的越南朋友是否考虑了他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人最终离开了西贡,越战结束了。 一段时间之后,我接到了老朋友内森·洛克菲勒不幸早逝这个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明尼阿波里斯的预言
“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用放大镜在地图上,找出了我可以去一所大学讲学的路径。 回绝了阿富汗司法部长的任命,熟悉阿明的阿裔美国法学教授告诉我,阿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他在阿推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苏联像美国当年陷入“越战泥潭”一样陷入阿战。 对驻美的苏联外交官而言,“冷战”期间在美国的旅行并非小事一桩,当然,对驻苏的美国外交官也一样。许多城市和地区是“不开放的”,甚至到“开放”城市的旅行也需要国务院的特许。有时,城市也许是“开放的”,但附近的机场和公路却是“不开放的”。 我就曾经遇到这一次这种情况,当时我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一秘,1979年夏天应邀到明尼阿波里斯大学讲学。在收到我的申请之后,国务院认为,虽然明尼阿波里斯对苏联外交官开放,但周围的道路和机场却是不开放的。但是,邀请单位并不打算取消我的这次讲学,自行坚持要求国务院找出可以使我成行的办法。此后,专程到华盛顿处理此事的大学代表告诉我,他们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将地图摊开在桌上,借助放大镜,终于发现明尼阿波里斯市周围的红线并未合拢,而在缺口处正好有一条铁路线穿过。这也许是监督人员的疏忽,没能将红圈画圆,但这却使我有可能乘火车抵达明尼阿波里斯。实际上,在这条荒废的支线上旅客列车在离城最近的车站每天仅通过一次,并且在凌晨四点。 我不得不先飞到开放的罗彻斯特市机场,然后乘汽车到荒无人烟的小站“红翼”,等待这趟火车。 我的讲课很成功,课后,我应邀与该校教授们一起共进晚餐。席间我的邻座是一位中年东方人。我们攀谈了起来。我的邻座告诉我,他是阿富汗人,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该校教授法学。 当天早晨已经知道,塔拉基在喀布尔被杀,阿明成为阿富汗新总统。自然地,我与邻座的话题——他名叫阿赫麦德——转到了这些事件。 “我很熟悉阿明,”我的邻座说,“他也在美国上过学,曾是阿富汗留美学生组织的主席。我们大家都清楚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新交在革命和塔拉基掌权之后没有回到阿富汗。 “曾经给过我司法部长的职位。但是,在了解到新政权上层的争斗之后,我回绝了,并决定暂时留在美国。” “我喜欢塔拉基。他似乎是个著名学者,可惜他死了。现在会怎样呢?” “我毫不怀疑是阿明组织了这起谋杀。”阿赫麦德说,“我还可以预测,现在会发生什么。他会将你们拖入阿富汗的战争。” “我们如何以及为何要这样作呢?” “您有没有想过,阿明从中央情报局领受了这样的任务?接下来,阿明马上会将自己打扮成莫斯科的忠诚朋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他会在国内开始加速社会改造,而这个国家依然生活在古老的教规和###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之下。建立“集体农庄”,没收大多数阿富汗人看作自己善主的地主领地,限制宗教自由,甚至试图过早地改变阿富汗妇女的地位——这一切就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也许,阿明的“改革”将会引起这个国家非常脆弱的行政机构内部分裂。将会开始逮捕那些阿明认为在“消极怠工”的人。同时,阿明会请求莫斯科派遣顾问进行援助。来自“不信神国家”的人将会进一步增强反对阿明制度的力量。届时喀布尔会向你们发出新的呼吁:派遣军事专家,此后是派军队。而克里姆林宫内部则未必会想起英国人“征服”阿富汗的厄运,和阿富汗人民抵抗域外奴役者的力度。你们的军队会很快进入,而你们也会在阿富汗得到自己长期和血腥的越南。可以设想,白宫内部将会如何高兴?对付“罪恶帝国”的说辞将会获得无限可能……” 对这个趣味盎然的阿富汗分析我以外交官的沉着回答说,虽然阿赫麦德的分析听上去有先见之明,但这些未必会兑现。 但是,回到华盛顿之后,我把此次与阿赫麦德的谈话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多布雷宁大使。他的反应相当特别: “你怎么能够让我把这种东西传到莫斯科去?昨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阿明,拥抱了他并且许诺在阿富汗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会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这样,我拟好的密电始终没有发出。可是即便克里姆林宫收到了,事情的进程会改变吗?就凭我国当时老朽昏庸的领导,1979年12月开始在阿富汗血腥的冒险未必会被制止…… 1983年,当我结束自己的外任回到莫斯科时,向当时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负责人阿尔巴托夫也讲述了此事,他嘱我就此为安德罗波夫写一份详细报告,其时后者在勃列日涅夫死后已经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不久,阿尔巴托夫告诉我,安德罗波夫认为这个信息有意义,并对它未能及时上报表示了遗憾。 然而,我再次自问,它会改变什么吗?毕竟安德罗波夫当时说话算不了数。
永不愈合的伤口(1)
作为苏联驻美国的外交官,我刚上中学的儿子却给里根总统写信,要求政治避难! 时值“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各大小媒体的歇斯底里毫无限度…… 为了我的儿子不被秘密送回苏联,里根总统亲自下令关闭美国的出境通道!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我的家庭跌入了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的漩涡。 狂徒的子弹撕裂了我儿子的生命,仅留下了一岁半的孙子,这是苏联解体之后。 此外,我还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是叶利钦总统的翻译。 “人的一生,绝不是坦途”,这是俄国民间智慧。每个人都会有沉浮苦乐。一个人的生活之路越长,便会愈加相信,每个顺利的时期之后命运一定会带来新的考验。 我差不多活过了这多事和血腥的世纪。在这期间经过多少事件!但人的天性,却在回顾往事时,首先想起来的,是风和日丽,虽然有不少的风暴急雨,乌云密布。正如许多国人一样,我本人曾经不只一次坠入深谷,而后似乎又一次开始新生活。所以,似乎可以原谅和忘却许多事,拿出勇气获得平衡。但是,有些伤口却在不断滴血,因为我们终究无法复活死者。 当我在华盛顿的“亚当姆斯”饭店奇迹般躲过了打劫者的子弹之后,似乎这是幸运再次垂青我的家庭。我继续自己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这使我有许多机会与美国学术界建立广泛联系。美国各地的同行经常邀请我讲座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与妻子瓦列莉娅,或者她自己喜欢自称列拉,我们到过许多州,建立了友谊,并且尽管有各种过度渲染的“冷战”因素,到处遇到了好感和热情款待。我们争取不漏过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和纽约林肯中心的每一个新剧目的演出,看了许多的新电影——当时有过不少的好影片。 我与列拉惟一的儿子,出生于1967年的安德列,在使馆的中学上学,课余时间与邻居的美国伙伴呆在一起。我们的房子不在用高墙与外界隔绝的使馆内,而是在首都绿茵茵的郊外切维·切斯,在一幢美国人的大楼里。与当地伙伴的交往帮助安德列很快掌握了语言。但这种交往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其中,我们对他热衷摇滚乐表示担忧,虽然他与同龄的孩子没有两样。在新年之前我们送给了他一把吉他,不久他已经弹得有模有样了。 在我们家住的楼旁边有一个公园,每逢星期天那里会爱好者举办的音乐会。安德烈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苏汉,黑发,25岁左右的东方年轻人。安德列其时已经满16岁,因此列拉非常惊讶,这二人之间何以有共同之处。安德列解释自己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