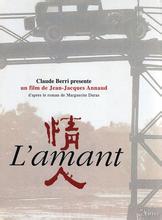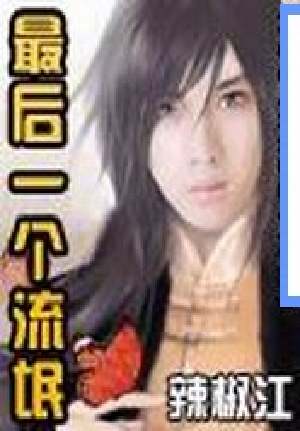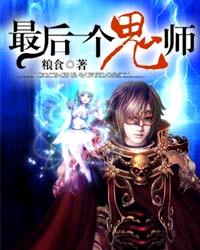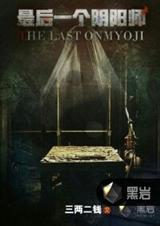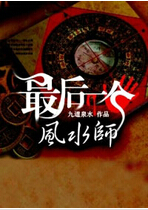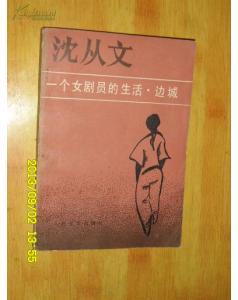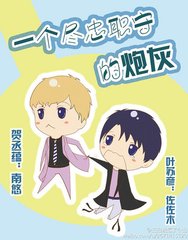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低的状况一下子有了改观。这些骨干力量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带动了各条线路面貌的变化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作为大型公交企业,与京、津、沪同行相比,在三项经济指标上都向前挪动了位置,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还破天荒地在1984年盈利164万元——这个数字也是空前的。夏任凡像窜出的一匹“黑马”,令人刮目相看,成为沈阳市的改革新星。1985年1月,夏任凡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十大青年改革者的头像,夏任凡排在第一位。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1985年4月,沈阳市交通局党委派整党联络组进驻电车公司,对夏任凡进行调查,并发动干部、群众对他进行“评议”。当年8月底,交通局又给夏任凡定了私长一级工资、用公家钱自己定做西服、违反财经纪律、违背中央政策、带老婆游山玩水等“罪名”。
夏任凡浮沉(2)
原来,在夏任凡到北京开会期间,一些人在电车公司一位领导人的支持下借机告了“黑状”,多封告状信送到了一位已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手里。这位在当地很有权威的老领导批示一定要调查。夏任凡到北京开“群英会”,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他准备回去大干一场,没想到,一回沈阳,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到家就受到了一遍一遍的“传唤”调查,紧接着经理的职务也被撸了。他如何接受得了?在家蹲了一个月“闭门思过”,有好几天卧床不起,高烧达到了40度,夏任凡越琢磨越冤,他想,一个小鸡子死了还挣蹦挣蹦,自己就这样完蛋了?
他偷偷跑到北京,找几位年轻的朋友述说自己的情况,问他们:“我究竟冤不冤?”熟人指点说,他应该找一个明白人问问。明白人在哪里?熟人说《人民日报》有一个艾丰可以试试。
就这样,夏任凡一路打听着闯到了艾丰的家里,介绍了来龙去脉之后,说:“人家说您是明白人,您看我冤不冤?您说不冤,我就认了;您说冤,我还想挣蹦挣蹦。”艾丰说,你做出什么成绩,你有什么缺点错误,最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夏任凡如实地直说了。艾丰听了,凭自己的新闻敏感,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如何对待改革者,特别是如何对待有缺点乃至有错误的改革者。但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听的又只是一面之词,不便表态。艾丰说:“第一,对你的事儿我感兴趣;第二,冤不冤我现在不能表态,因为只听了你一面之词。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到沈阳去作调查。”
艾丰的话是认真的,和其他同志一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个题目不错,有新闻价值:改革者受“陷害”,很具有典型性和时代意义,媒体应该介入予以关注。于是艾丰打点行装后直接“杀”奔沈阳。
关键是如何掌握真实情况。为此记者要防止先入为主,于是艾丰使用“反调查”的办法。他先到了直接负责处理夏任凡的市交通局纪委书记处,请他介绍夏任凡的问题;再找到沈阳电车公司现任党委书记,请他介绍现任党委对夏任凡的看法;然后又请公司党委召集一些人座谈。对召集什么人,艾丰提出了一条要求:“找平时对他意见最大的人和最了解情况的人。”
《人民日报》记者来调查,这在电车公司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交通局和电车公司新班子都很紧张。对参加调查会的人,新任电车公司党委书记事先一个一个地做了布置:一定要给记者一个强烈的印象,夏任凡错误严重,不仅不能再回来复职,还要加重处理。果然,会上众口一词,愤怒地揭露夏任凡犯下的种种错误。会议结束后,人们一哄而散,艾丰被晾在了那儿,既没人招呼去吃饭,也没人送他回住处。艾丰知道,在他们的眼里,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调查了几天,夏任凡“毛”了:怎么专找反对他的人谈话?难道不是来为他说话的?现任党委书记也“毛”了。记者听了这么多情况,为什么还不表明态度?他沉不住气了,就对艾丰说:“前段时间来了个《青年报》的记者,这家伙,到我们的基层乱说一气,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这样的记者我们不欢迎!”艾丰明白,这是借说别人来教训自己,心里有点恼火。他看着这位30多岁的书记慢悠悠地说:“我参加新闻工作的年头也不太长,大约30多年了。这些年我在工作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到一个单位采访,就怕听到不同的意见。如果关于一件事,有的人说是黑的,有的人说是白的,我究竟怎样写呢?那时候我就没办法了。现在工作的年头多了,正好倒过来。如果到一个单位采访,关于一个问题听到的都是一种意见,我就要格外警惕。因为对任何事情,一般都是两种以上的看法,为什么这里只有一种?肯定是有一种外力压制着另一种意见,不让人家发表!”此语一出,书记的脸上立时有些变了颜色。
艾丰下决心把情况搞清楚。在沈阳电车公司整整采访了14天,每天从早晨谈到夜里12点以后。因为宾馆到12点就没有热水了,所以艾丰14天没洗澡。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夏任凡浮沉(3)
艾丰的思路是这样的:与反对夏任凡的人包括最反对他的人都谈过了,看他们提供的事实到底够不够把夏任凡撤职,如果够,夏任凡就不冤枉,如果不够,就是冤枉的。了解到最后,艾丰心里有底了,真正板上钉钉的出在夏任凡身上的问题没有一件可以达到把他撤职的程度(诸如夏任凡在香港买了房、在那里有了女人等,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故事”)。
有了这个底数,他又找支持夏任凡的人作调查。通过这方面的调查他清楚了,对夏任凡意见的增多,是矛盾激化造成的;矛盾激化是公司改革权力和利益调整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而夏任凡对此又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问题的性质也有了底数。
问题了解清楚后,艾丰约见了当时的沈阳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汇报过采访到的情况后,艾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夏任凡是一位年轻的改革者,如何对待这类人的缺点和错误,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我想写一个内参,发一篇公开报道。内参和报道写好后再送你们审阅。”这位领导同志很和蔼地接待了艾丰,听了事情原委以后表示:“你调查得很细,有一些情况连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今后将抓紧解决这些问题。内参和公开报道,我建议都不要发。因为电车公司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全市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它,如果发表以后,造成了思想混乱,可能影响全市的大局。”艾丰很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良苦用心,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夏任凡在改革中有成绩,而上级对他这样处理,人们肯定会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这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的继续进行,已经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通过媒体报道,澄清了是非,不是更有利于团结和改革的进行吗?当然,为了利于实际工作,内参和报道都先不发表,等你们有了一个新的处理结果之后,连同你们的结果一并宣传报道。您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一定向编辑部领导汇报。”
艾丰回到北京,新的处理结果一直没有消息,但另一方面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交通局和公司党委对夏任凡的整治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加强了监视和歧视——谁和他说话都得向公司的领导汇报,而且声言要对夏任凡加重处分!
艾丰心情很沉重:问题没解决,反而害了人家,这岂不是一件太遗憾、太令人不安的事情吗?有良心的记者,不能就此撒手不管!
于是艾丰决定二下沈阳。他事先把报道写好,打印了三份小样,公司送一份,市委送一份,交通局送一份,并做了一个简单说明:请你们过目,事实有无出入?观点有无问题?如无意见,本报拟发表。沈阳市委主要领导换了新的人选,委托宣传部门领导审阅了稿件,认为事实无误,观点没问题,但还是不同意公开发表。
于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稿件经过审阅后艾丰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有五位沈阳的同志赶到人民日报社。传达室的同志告诉艾丰说,沈阳有人来找。艾丰感到很奇怪,刚从那里来,怎么就有人来找了呢?一问原来他们是拿着艾丰写的稿子的小样来找报社领导的,来人不知道报社领导的名字,所以就出示了小样。而传达室一看小样上有艾丰的名字,以为是找他的,就给艾丰打了电话。艾丰立即明白了他们是来“告”自己的,不过艾丰认为他们是为公事而来,于是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还把他们引见给报社领导,请他们直接向报社领导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最后,报社领导根据全面情况还是决定公开发表,于是《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夏任凡免职前后》在1986年6月16日见报了。此报道在当地以至全国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来信,热情拥护和赞成报道提出的正确对待改革者和爱护改革者的问题,以此报道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也形成了保护改革者的舆论氛围。经过半年的时间,在中央的过问下,夏任凡的处理问题得到了解决,取消了对他的撤职处分,将其换到另一个单位——沈阳长途客运汽车公司担任同级别的职务。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夏任凡浮沉(4)
尚未结束的争议
对于如此艰辛产生的作品,艾丰在《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回忆了写作这篇《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的构思:
就本文来讲,其实质性的意图,是通过说明对夏任凡处理过重这一事例,告诉改革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更要告诉各级领导,为了不断推进改革的事业,要十分注意慎重地对待改革者的问题,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报道并没有只是就写这一面,仅仅说夏的“好话”。全文分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说夏的成绩。第二部分说夏的缺点和问题,这一部分的长度和第一部分差不多。按说本文是为夏说话的,还说夏本人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干什么?按过去单侧面报道的思想,是不会这样写的,但根据多侧面报道的思想,我这样写了。这样写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第三部分写主管机关对夏的处理,既写了他们处理对的一面,当然更指出了处理不恰当、不对的一面。
艾丰认为,这种多侧面的写法,有三方面的好处: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对被批评者来说,他们也会觉得记者是真正为了搞好工作来进行批评的,即使是要批评某一个人,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对记者基本肯定的报道对象来说,既有保护他的作用,也有提高他的作用。
事实表明,这一多侧面的报道无论在作品本身的宣传效果和实际工作的改进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写完《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后,艾丰觉得还不过瘾,1987年再下沈阳采访夏任凡,并于1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追踪夏任凡——沈阳采访札记》一文,借此来进一步深刻剖析社会该如何看待时代改革者的问题。文章开头第一段就说:“曾被免职的改革者夏任凡,终于走出了前进路上最狭窄的夹缝。改革者气候正好。但千千万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