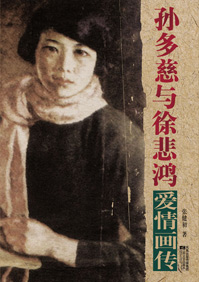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命令方策率陆军第六师速达安庆接防;方鼎英率陆军第十师速达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将方植之、苏宗辙、孙传瑗逮捕,押送南京。
方振武乘坐的安丰舰,恐怕还没有驶出安徽的江面呢,孙传瑗就在家中被押走了。
安庆五大城门之一的盛唐门,民间俗称小南门。现不存。
1929年的第一场秋雨,在这个夜晚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秋雨夹着秋意,带有一种无言的苍凉。恰恰又逢上停电,烛火在风中摇曳着,忽儿明,忽儿暗。没有父亲身影的客厅,更显得空空荡荡。
孙多慈坐在母亲身旁,轻轻为母亲拭着眼泪。
“你爸爸被带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让你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学业。”
“我知道。”
“你爸爸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你身上,可别让他失望啊!”
孙多慈没有回答。但那一刻,十七岁的她,知道自己长大了。
相比之下,这年秋天的安庆之乱,远比孙多慈家庭之乱来得狂野。方策率陆军第六师应蒋介石之令接防安庆时,本已率军南下继任安徽省主席的石友三,突然被改派赴两广与李宗仁、陈济棠部作战。石友三强烈不满,于是10月在江苏浦口发动兵变,重兵围攻了南京城。这之前的9月28日,已驻防安庆的石友三部秦建斌师,因怨恨方策陆军第六师对他们的牵制,也在安庆城发生了骚乱。不过安庆这场骚乱的性质,更接近于一场兵灾。
孙多慈目睹兵灾的全过程。
那天下午放学,孙多慈绕道到刘松林笔店去挑一支水笔。已经往家里走了,在四牌楼胡玉美酱坊门口,就听见身后一片骚动,马上就有人一脸惶恐奔过来,“不得了啦,士兵在店铺里抢东西啦!”
一街人都把脖子伸长往后看,“哪家?哪家?”
“还在海华鞋店呢,一街的店子都被抢空了,柜台也被掀翻了!”
还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见一群身着黄军装的持枪士兵,大摇大摆由国货街转过弯来。军装之“黄”,黄得蛮横,黄得无理,刹那间,窄窄的四牌楼被这“黄”给浓浓罩住了,成为灾难之地。
商家的老板、伙计也顾不得许多了,“辟哩啪啦”纷纷抢上门板。而没来得及关门的商家,那些急红了眼,已经撕开脸皮的士兵,枪一横,就直接冲了进去。老板态度好一些,他们还慢条斯理从货架上拿。稍有反抗的,抬起枪柄就朝柜台上砸。沿街的华利鞋店、三捷鞋店、久大恒绸布店、永聚恒百货店,不管需要还是不需要的东西,只要是能看到的,统统都揽到自己怀里来。亨得利钟表眼镜店里的那些钟表眼镜,更被洗劫一空。宝成银楼、正泰昌银楼和宝庆银楼虽是士兵眼热的对象,但三家门户坚固,早早地就关起来了,士兵们用尽方法,也无法将它们砸开。
面对这一切,孙多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呆呆地立在那儿。还是一位过路的长者暗暗推了推她,“这是个是非之地,你一个女学生,还不快跑啊!”这才醒悟过来,气喘吁吁跑回汪家塘。
晚上就有各种消息传过来,说西门外也有军队起事了,他们冲进河街上的厘金局,想撬开里面的保险柜,结果没有得逞。厘金局的局长张啸岑,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听到消息,当场就吓得小便失禁。又说有另一批士兵在北正街省立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强行带走了十多位女学生。出城后,有一位女生拼死拼活不愿意,结果被一枪打死了。陆军第六师师长方策,也在这场兵灾中被掳走,后被挑断脚筋,成了个废人。
那一夜,整个安庆城人心惶惶。
半夜里,孙多慈从噩梦中惊醒过来,在梦中,她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女学生。
难道这就是父亲梦想参与的政治?实在是太可怕了。在她的想像中,政治应该是和鲜花、掌声、列队欢迎的锣鼓联在一起的。而她目睹的这一切,包括父亲的被抓,实在是太丑陋,太卑鄙、太黑暗、太险恶了。
几乎同时,作家郁达夫接受省立安徽大学邀请,担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9月29日中午,郁达夫从上海乘船抵达安庆。10月1日,郁达夫专门转到大南门内正街,在当年曾经来过的一家清真餐馆吃了午饭,后来又到东门的城头上转了一圈。10月6日,安徽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他为赤化分子,并列上政府重点清查的黑名单。闻此消息,郁达夫吓得半死,立刻赶到了招商局码头。“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后来他在日记里说。
10月8日,郁达夫从安庆回到上海,夫人王映霞见怪不怪。去安庆之前,她就担心他的工作会有变故,所以买的是来回票。不过让她恼火的是,也不至于走得匆匆,连行李物件都丢在安庆。不得已,王映霞只好自己去了一趟安庆,不仅代郁达夫向学校要到了一学期的薪金,而且也把他的行李给取了回来。
虽然只去过安庆一次,王映霞却深深记住了这座江北城市。
。 想看书来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1)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带着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孙多括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在大观亭之上,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南岸那远远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经满十八周岁了。“倚槛苍茫千古事;过江多少六朝山。”面对大观亭门柱上这副对联,她停步良久,心中也生出许多苍凉的感慨来。
几天后,父亲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他们将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一家,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分开三个月之久的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从下关大轮码头下船,踏上南京城的街道,孙多慈突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她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但她感觉,这座城市,与她,与他们一家,肯定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原以为父亲肯定是一副萎缩潦倒之象,甚至想像他完全变了个人:两颊瘦了下去,眼睛也凹得多深。在家里基本看不到的胡须,又深又长,挂满两腮。关键是他眼中充满激情的锐气消失了,替代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是绝望的惆怅。但让孙多慈没有料到的是,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打垮父亲,反而在他身上,生出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威武不屈之气。
顺着长长走廊走过去时,父亲正在斗大监室之中,消消停停地与监友下棋,看他神态怡然自得,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阶下之囚。明明知道夫人带着三个孩子来看他,也不回头,倒是他的监友一再提醒,并且把棋盘推了,这才逼他回转身来。
看见父亲,孙多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你这傻孩子,哭什么。”孙传瑗笑着将她拉过来,“来,介绍你认识蒋叔叔。蒋叔叔蒋方震,字百里,地地道道的民国奇人。你读过的《浙江潮》、《改造》,中国一流大刊物,都是他主编的!爸爸此次能与他同监,是三生有幸!”
蒋百里的名字,孙多慈有所耳闻。报刊介绍他是军界奇人,有“中国兵学泰斗”之誉。这位光绪秀才,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回国,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又赴德国学军事。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其主编的《改造》杂志,在国内的影响,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倾注他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十六套八十六种,是民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都是在共学社出版的。1929年末,因参与唐生智联手石友三的反蒋活动,也被蒋介石秘密关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孙传瑗对蒋方震说,“我这个女儿孙多慈,是我的最爱,常和你说‘平生爱女胜爱男’,指的就是这个丫头。”
孙多慈礼貌地与蒋百里打招呼,但她的眼睛里,泪水依然无法止住。
孙传瑗不高兴了,把脸一沉,道:“还记得孟子《告子》关于‘动心忍性’那一节吗,来,背来给我听听。”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孙多慈一边哽咽,一边背诵出来。
孙传瑗满意地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实。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从小就和你讲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艰苦磨炼。家庭变故,人生坎坷,环境恶劣,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磨炼人,造就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修养人格,坚强意志,致力学问,创造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至大至刚,塞乎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吗?”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2)
孙多慈半跪在父亲身边,一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
“好,你给我记着,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抓紧时间,认真准备,还是按照我们原先订的计划,报考国立中央大学。”
在安庆女中,孙多慈一直是学校的骄傲,国文、数学、英语三门重点课目,只有数学略差一些,另两门始终是高分。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安庆女中的校长也把孙多慈当作一面旗,无论校内校外,大会小会,总是得意洋洋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我们安庆女中有两位才子,一个苏雪林,现在是安徽大学的教授了;另一个孙多慈,将来还不知道如何发达!”
1930年是孙多慈命运转折关键之年,随着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做了细致的商量,当时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可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短短两个多月下来,各课成绩直线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