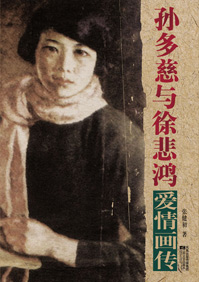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支持派。
1934年大风之夜,孙多慈写《李家应》。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荒牛,你是落水狗,你当真还能大得过我?”
李家应老家在安徽含山,父亲李立民与孙多慈父亲孙传瑗一样,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庆的。民国之后,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过多年。后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家小一直放在安庆。李家应个头与孙多慈相仿,但略壮一些,性格也更直爽。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个人情感等,也比孙多慈要果断。她的这种性格特点,七年之后在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会长是宋美龄,浙江分会会长蔡凤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夫人。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在李家应打理下,短短几年,成绩突出。1942年春,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奉宋美龄之命,专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这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服饰华丽的俄罗斯籍女士,对李家应的工作称赞不已。1943年,日军逼近丽水,李家应率保育院迁至云和县,1944年又迁往平阳。尽管条件恶劣,李家应还是带领全院教职员工,垦荒千余亩,办起了农场、畜牧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此外,他们还修建校舍,创办工艺组,自己动手织布、做鞋、缝纫、织袜,基本解决了师生生活所需。此时的保育院,实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农场学校。1945年8月,李家应因身体欠安,离开第一保育院,相处七年的学生闻知,相送三十余里,一路哭声不断。1945年10月,李家应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八年胜利纪念勋章。
当然,此是后话了。
李家应也是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闺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此时,也是孙多慈相对苦恼的时期。于是,更多时候,李家应只是一个倾听者。
正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新生,孙多慈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徐悲鸿对自己若近若远,若即若离,似乎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那段时间,他极少约孙多慈去他的画室,有时孙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态度也不比往日。虽谈不上是冷淡,但也绝说不上是热情。他总是处在绘画创作状态,与孙多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即使说了,也不在路子上。孙多慈很失望,如果徐悲鸿真对自己穷追猛打,她可能无所谓,不觉得这是什么快乐或幸福。但徐悲鸿对自己不冷不热,在感情上,她又一时接受不了,心里面始终空荡荡的。抬眼看头上的天,垂首看脚下的地,感觉都是灰蒙蒙一片。
孙多慈是无遮无掩的人,她的这种情绪,在闺中密友李家应面前,自然都表现了出来。
李家应认为孙多慈爱情之途险象环生。“如果真想和徐悲鸿相爱,在你心理上,至少要冲破三道障碍:一,年龄的障碍,他毕竟比你大十七岁,做得你的父亲了,现在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你四十岁、五十岁时,想想看,他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你能适应这种年龄差距?二,道德的障碍,师生恋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又是与徐悲鸿这样知名画家的师生恋,负面影响更要加倍。前期你们还没有闹出什么,小报记者就编了那么多花边新闻,如果真有什么故事,还不把一个南京城给炒翻天?三,家庭的障碍。你这边是你父亲的反对,他那边是他夫人的阻挠,尤其是他那个夫人,据说特别凶狠,你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怎是她的对手?” 。 想看书来
十一、 闺中密友(2)
孙多慈“扑哧”笑出声来,“到底是社会学系的高材生,说出话来,也一套一套的。哪有那么严重,我只是和他交往密切而已,暂时还没有超过师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在乎他对你的态度。”
“不在乎也是假话,我是学生,当然希望得到老师的宠爱;我是个女学生,也当然希望得到男老师的关爱。人之常情嘛。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期待与他在感情上能有什么发展。”
李家应说,“我有个馊主意,装作听取他的意见,说有男学生在追求你,和他半公开摊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孙多慈不以为然,“这种下三烂的方法也拿得出手,他不笑话你才怪呢!”
“也只是试一试嘛,并不伤害你什么,也许有效果呢?”
孙多慈想想也对,就按李家应教的方法,到徐悲鸿画室,故意轻描淡写地把这事说了。
徐悲鸿并不接她的话头,笑笑,故意说起了另一件事,“昨天还是前天上午,有一位青年,经老朋友介绍,到我这里来,说要学习绘画。我看他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就料想是哪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于是我对他说,‘绘画是小技,但可以显至美,造大奇,非锲而不舍,勤奋苦学不易成功。’我又对他说,‘还需要有一种准备,即使你学有成就,在当今的社会里,未免有饿肚子的忧虑,所以还要有殉道者式的精神,必要时要把整个生命扑上去。’那位青年听我说得如此恐怖,凳子也坐不住了,赶紧溜了出去。”
孙多慈先还不明白徐悲鸿的意思,也跟着傻傻地笑了笑,后来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寓意,脸马上红成一团,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徐悲鸿走过来,抱住了她的臂膀。“你放心,老师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现在你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份变了,关系变了,环境也变了,有些事,就必须避一避。这一阶段,外面风言风语传得厉害,我家里那一位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如果真闹开来,徐悲鸿个人得失事小,你的前途事关重大。所以在近两三年内,我想,还是把我们的感情放一放。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来。你是我极力推崇的学生,如果你的画技两三年没有长进,出不了成绩,你让我对外界,怎么解释这一切?你那图画满分的佳话,岂不真要成为徐悲鸿一生的污点?懂吗?多慈!”
孙多慈是乖巧女孩,自然很快就领悟了徐悲鸿的这番良苦用心。而她更感动的,是他最后那一声亲切的“多慈”,似乎是一盆火,能把她整个身体,都实实在在地融于其中。
后来孙多慈把徐悲鸿的反应说与李家应,李家应也感到敬佩,“徐悲鸿教授是真汉子,一生有这样的男人为知己,死也足矣!”她从心里发出感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孙多慈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的高峰阶段。晚年她向子女讲述这段往事,总是眯着眼睛,一片得意之情,“那时候,脑子里真的一片空白,除了学习,学习,还是学习。在学校里,我的生活路线基本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图书馆——教室——宿舍,甚至星期天也不逛大街。”除了美术专修科的专业课以外,她还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选修课程很满意,他对她说:“胡小石是国学大师,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古诗选》,堪称中国第一。你喜爱古诗词,肯定获益匪浅。徐仲年是我们教授会主席,翻译家,鲁迅的《呐喊》,就是他译成法文推荐到国外去的。盛成的《我的母亲》能不能读好,就看你跟在他后面学得如何了。”又开玩笑说,“宗白华的《美学》,恐怕是出于老乡和前辈的面子才选的吧。”见孙多慈开口要辩,他笑笑道,“当然是一句笑话。在国立中央大学,在美术专修科,不选修宗白华的《美学》,专业课再好,也不能及格。宗白华可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哦!说来有趣,美学界‘南宗北邓’,都是你们安庆人,而且与我关系都不错。‘南宗’宗白华算得上是至交,‘北邓’邓以蜇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之后,记得你曾经说过,七扯八算,你们还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呢!前些天去北京,我还专门拜访了邓以蜇,欣赏了他珍藏的完白山人的书法作品,那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康有为说‘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皆能为篆’一点不假啊!有机会去北京,你也要好好学习。完白山人邓石如,在你老家安庆,应该算第一名人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一、 闺中密友(3)
那时候,中央大学有四位裸体模特,其中一位是上海请来的,另外三位,都是南京本地挑出来的少女。孙多慈习惯了临摹石膏像,第一次面对真人,多少还有些不自然。一些男学生的眼光,也怪怪的另有一种色彩。徐悲鸿对模特很尊重,上课之前,总是向模特行注目礼。他也要求学生们对模特的献身艺术的精神表示尊重。
圈外的人对模特总有其他的联想,不少外系的学生谈至此,还有一些不理解,那天在食堂,几位同学为此相争,有一位老夫子居然怒气冲冲,“既然是实物写生,为什么偏要裸体人物?狗啊猫的,也同样可以用嘛!”
孙多慈在这边桌子吃饭,本来可以不多事,但听至此,实在忍不住了,立起身来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这是徐悲鸿授课时的原话,孙多慈在此只是照搬,但合乎情合乎理,掷地有声。
争论的几位同学不出声了,一起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这位冷美人。
后来孙多慈拿此事在徐悲鸿面前表功,徐悲鸿果然高兴。又感慨说:“现在的社会,封建残余思想盛行,鼠目寸光者,少见多怪者,比比皆是!尽管不合时代潮流,但想彻底转变,也非易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共同努力吧。”
这年年底,徐悲鸿一家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
吴稚晖出资为徐悲鸿买下的这片宅地,在鼓楼坡之北,之前是一片荒凉的坟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随“建设新首都”计划启动,南京地产业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地价飞涨。三千块大洋在当时不算是小数目,但在傅厚岗,也只能勉强圈下两亩地。南京老人回忆傅厚岗,都记得徐悲鸿公馆内的两棵大白杨,树干有十数米高,树冠如盖。徐悲鸿新建的画室,就坐落在两棵白杨的树阴之下。类似的巨大白杨,南京城只有三棵,另一棵在城南。当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火车徐徐驶进下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们。
徐悲鸿公馆未落成之前,孙多慈拉着李家应来看过多次。这是栋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建筑主体为欧式风格,但中间又糅进了有中国传统的庭院色彩。别墅下为客厅、餐厅,上是主人的卧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为宽敞的庭院,四周以篱笆筑成隔墙。
孙多慈她们并不敢走近,立在街的这一边,遥遥相望。更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