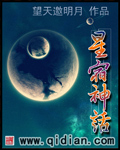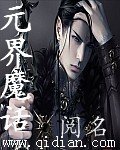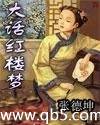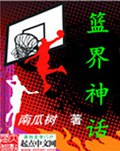无稽的诗话-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整首诗的比较上看,钱先生所举的诸位大诗人的诗,无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是难以与王安石的诗相媲美的。这些诗作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不仅选篇极严的《唐诗三百首》全不收录,甚至连选篇上千的《唐诗选》及《唐诗鉴赏辞典》等大型有影响的文学选本也未加以收录,而王安石的诗脍炙人口,有本则选,这种“选本现象”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诗作品位不高,大逊于王安石了。再从诗的具体内容上看,这些诗为写景而写景,境界不高,题旨浅薄,写的无非是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趣,纵然也把形容词“绿”用作了动词,以表现春风的形象,但读来平平淡淡,丝毫引不起人们的激赏。而王安石的诗,情景交融,立意高远,既描绘了江南美丽的春色,又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感时思乡,深挚动人,正如《彦周诗话》所评:“超然迈绝,能近李杜陶谢。”而“绿”的运用,对于整首诗而言,更是锦上添花。一个“绿”字,堪称一篇诗眼,能使整首诗生辉添彩,那些前辈所用之“绿”,又怎么能与它相提并论,又怎么可以用“袭用”、“暗合”来否定它的炼字的富有创意呢?
再从修辞学的角度作横向比较。这里不必再赘述人们所熟知的“绿”在色彩、形象、情感诸方面大胜于“到”、“过”诸字的妙处,仅就臧克家先生提出的含蓄与显露的问题作一分析,也可见二者的高下优劣了。
臧克家先生认为,“到”、“过”含蓄,“绿”直露,前者可以使读者想象出春天更多的色彩来,而后者则限制了春意的丰富内涵。不错,从表面上看,“到”、“过”没有将春天的景色具体化,因而留下的想象余地大,似乎比“绿”含蓄。但实际上,“到”与“过”的所谓含蓄不过是表现力的苍白而已。由于它们本身只是没有色彩的一般常见的动词,因而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在字词大都平淡的诗句里,处在关键的位置上,就很难给读者的想象力以强烈的刺激,从而使读者对江南的春色产生五彩缤纷、花红柳绿的丰富联想。如果王安石用了这些字,那么诗句就平庸无奇了。而“绿”色彩鲜亮夺人,不仅没有“到”、“过”的苍白、单调,相反地,它相对春景的丰富多彩而言,其本身也是含蓄的。因为春天的色彩绝不仅是绿色一种,它还有难以尽数的万紫千红,“绿”不过是其中最具化表性、最为惹眼的一种罢了。从修辞的角度看,“绿”是以局部代整体,它以自身的鲜丽炫目的色彩,为读者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刺激源,从而激发起读者对江南春色作无限丰富的联想,这怎么能说“绿”“显露而不含蓄”呢?
综上所述,钱钟书先生和臧克家先生在对“绿”的纵横比较的否定中,着眼点太拘泥于形式,太重外在的因素,论证难免失之偏颇;而历来人们对“绿”的鉴赏也大都太偏重于锤词炼字的形式上的推敲。其实,“绿”的最大妙处,“绿”的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它的源自客观生活的真,是出之于自然,得之于天籁的。我们知道,诗人写的是大地尽绿的春日盛景,而“到”侧重的是“刚来到”的早春之景,“过”侧重的是将过去“暮春之景”,“入”太单调,似乎春风只吹过一溜,“满”固然充实,但又缺乏春天的具体可感性;唯有这个“绿”字才能把诗人眼前的美丽春光真真切切、具体可感地描画出来。诗人站在行驶于“京口瓜州一水间”的渡船上,满怀深情地回首眺望“只隔数重山”的钟山,弥望的景色只能是无边无际的一片浓绿,那紫那红……,都掩映于浓绿的树木下自然难见其色。可以说,“绿”写的就是诗人眼中之实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就美在自然上。
《阅读与写作》1995年第1期
《高师中文信息资料》转摘。 最好的txt下载网
无稽的诗话
历代诗话中记述了许多古代诗人诗词创作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成为文坛创作的佳话而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不仅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所津津乐道,而且也常常被严肃的文学研究者当作文学研究的史料加以不断地引证。其实,有许多著名的诗话不过是诗话作者的向壁虚构,无稽之谈,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精心创作。这些诗话大都不见于正史,
而仅仅见之于文人的诗话词话和笔记小品类的著作之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文学的野史罢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诗话对于诗歌的普及,对于提高人们的创作与欣赏的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正本清源,指出其真伪,还这类诗话以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以讹传讹,还是很有必要的。
“推敲”是流传最广的一则诗话了,但这则诗话却是最无稽的。据宋曾的《类说》转引《唐宋遗史》记载,贾岛因《题李凝幽居》诗第四句中的一个字是用“敲”还是用“推”而苦思冥想拿不定主意,于是骑着驴在路上反复作着推敲的样子,结果一下子撞着了京兆尹韩愈,而韩愈却不计较他的冲撞,反而帮助贾岛修改他的诗作,并将诗定为“僧敲月下门”,而且二人就此结为诗友。这则典故常常被人们作为贾岛诗歌创作刻苦认真的苦吟精神的例证以及古代诗人锤词炼字的典范而不断地引证,很少有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查一查二人的生平传记,就可以知道,韩愈做京兆尹时,是823
年,而韩贾二人的初交却在811年,即在“推敲”故事发生的前十多年,那时二人就已相识相交了,并有许多诗歌相互赠答,怎么可能在十一年后,二人在京城大路上相遇而不相识呢?再者,这故事本身也很不合情理,不合文学创作的规律。锤炼诗句,选用什么字词,主要取决于更生动、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即字词的选用是由生活本身来决定的,而非主观臆断。因此“推敲”二字的选择,应该由生活的真实情况来决定,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断呢?贾岛苦思冥想已属做作之举,而再由韩愈这样的没有这种幽居生活经历的人来作判断。就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了,这实在是有些问盲于路的滑稽。
其实“推敲”二字各有意趣,各有千秋,而且二字内涵的差异也特别大,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只能是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这已不是纯粹的语言技巧的问题了。如果当时贾岛夜访时是推门而入的,那就该毫不犹豫地用“推”。如果当时是敲门,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用“敲”。用“推”,意在表现僧人幽居,门无需插,那鸟宿池边树时推门的“吱呀”一声,也是非常富有情趣的。用“敲”也有其道理,贾岛夜访,本不知其门是插还是未插,“敲”便是一种很自然的动作,那夜深人静时的清脆的敲门声,也是十分令人心动的。到底是用“推”还是“敲”,也只有贾岛心里最为清楚,又何劳韩愈予以定夺呢?而贾岛如此煞费苦心地苦吟,
实在有些矫揉造作,如此违背生活真实的苦吟,已是入了咬文嚼字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歧路了,是不值得后人效法的。从这个角度看,这则诗话的编撰者,实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实在是帮了贾岛的倒忙。而后人竟然信以为真,并经常以此来印证诗歌创作的理论,确实是大谬不堪的了。
苏轼,秦观,黄庭坚,佛印四人为杜甫的《曲江对雨》诗补字的诗话,
也是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这则诗话的真实性同样也经不起推敲。这则诗话见于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的注引,说四人见一处院壁上写有杜甫的诗《曲江对雨》,其中的“林花著雨燕脂湿”句的“湿”字为蜗涎所蚀。于是四人各补一字,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虽各有意趣,但找来杜甫的诗集一看,又都觉得不如原诗的那一个“湿”字。的确,杜甫的一个“湿”字,把四人的字意都包括进去了,而且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写绝了林花着雨时的难以言喻的美。而四人的补字,恰恰从反面,有力地烘托出了“湿”的深蕴的审美内涵,显示了老杜非凡的炼字功力。这则诗话,确实是讲解诗歌炼字之妙的绝好例证。不过,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且不说四人同游此处院落的历史真实性如何,也不说他们补的这四个字着意在显示四人各自的“生老病苦”的人生哲学,迥异不同的性格特征,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四人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对于古典诗歌都有着极深的造诣,他们对于上一朝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作品,理应是非常熟稔的,特别是对他们的名作,更应该是倒背如流才是,这对此四位素以博闻强记著称于世的文坛大家来说,不仅不是难事,而且正应是其特长。可是面对着杜甫的诗歌名篇《曲江对雨》,这四位宋代诗坛上的佼佼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记得清这首诗的名句中最为关键的作为诗眼的一个“湿”字,显然在情理上无论如何也是讲不过去的,其人为编造的痕迹,也就不言自明了。
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绿”字的炼字佳话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但诗话真实与否,也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它出自洪迈的《容斋续笔》,材料的来源据说是“吴中士人家藏其草”。且不说古代诗人写诗时特意把草稿留传下来,并传之于他人的事例实属罕有,单就其草稿的内容来看,也有多处令人不解的地方。草稿上这样写: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王安石好改字确是事实,但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这个”绿”字,要作如此改法,却又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首先,“绿”字形容词作动词用,这种词类活用的炼字之法,在古典诗词中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并不少见。如丘为的“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的“主人山门绿”等等,作为对古典诗歌有很深造诣的大诗人王安石来说,不应不知道这些常识,而且他自己还写过“除却春风沙际绿”的诗句。“绿”字的选用,原本不应当是多么玄妙的事情,甚至也不应该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因而用了十数字才选定这个“绿”字,从情理上说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再者,在诗稿上圈去字时,竟然还注上“不好”两个字,似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既然已经圈去了,又何必特意多此一举地注上“不好”二字,好像故意要让外人知道他的思考过程似的。还有,被圈去的十多个词,都是常用的动词,类似的可列出几十甚至几百个,这样漫无目的的并不太复杂的选择,有什么必要一一都罗列在纸上呢?如此做作,倒实在有些像玩文字游戏了。臧克家说得好,这些字其实都各有千秋,像诗话说的那样,选来选去的,只能说明诗的笨拙罢了。但一般人谈到这个诗话,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从那么多的字里选择到这样一个字,实属罕见,显示了极强的非凡的炼字的功力。其实,像王安石那样的大诗人,怎么可能这么拙笨,为了一个并不稀罕的字,而罗列出那么多的平庸之字?细加推敲,可以看出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它极可能是说诗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