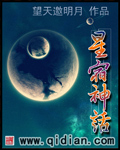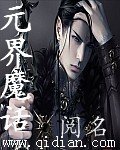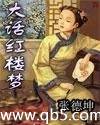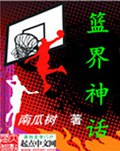无稽的诗话-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落花有真意 流水亦含情——卞之琳《断章》诗赏析
论诗者大都把卞之琳的《断章》看作是一首意蕴艰深的哲理诗,其实作为言情诗来读,诗味才足呢!那优美如画的意境,那浓郁隽永的情思,那把玩不尽的戏味,那独出机杼的题旨,细细品来,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诗是这样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诗的上节撷取的是一幅白日游人观景的画面。它虽然写的是“看风景”,但笔墨并没有挥洒在对风景的描绘上,只是不经意地露出那桥、那楼、那观景人,以及由此可以推想得出的那流水、那游船、那岸柳……它就像淡淡的水墨画把那若隐若现的虚化的背景留给读者去想象,而把画面的重心落在了看风景的桥上人和楼上人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了这两个看风景人在观景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那种极有情趣的戏剧性关系上。
那个“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面对着眼前的美景,显然是一副心醉神迷之态,这从他竟没有注意到“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的侧面烘托上就可看出。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显然也是为“看风景”而来的楼上人,登临高楼,眼里所看的竟不是风景,而是那个正“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这楼上人为何不看风景专看“你”,是什么深深迷住了那双眼,是什么深深打动了那颗心?这耐思耐品的一“看”,真可谓是*蕴藉,它使那原本恬然怡然的画面顿时春情荡漾、摇曳生姿,幻化出几多饶有情趣的戏剧性场面来:那忘情于景的“你”定是个俊逸潇洒、云游天下的少年郎,那钟情于人的楼上人定是个寂寞思春、知音难觅的多情女,一个耽于风光,憨态可掬,孰不知一举一动搅乱了几多情丝;一个含情脉脉、痴态可怜,可心中情眼中意羞言谁知?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而在人生旅途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萍水相逢、一见钟情、转瞬即逝而又经久难忘的一厢恋情啊!而诗人正是以这短短的两行诗给那电石火花般的难言之情、难绘之景留下了永恒的小照,引人回忆,激人遐想。
诗的上节以写实的笔法曲曲传出了那隐抑未露的桥上人对风景的一片深情,以及楼上人对桥上人的无限厚意,构成了一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戏剧性场景。但多情总被无情恼,那无情的风景,那忘情于景的桥上人能否会以同样的深情厚意,来回报那钟情于己的多情之人呢?面对着生活中这司空见惯的、往往是以无可奈何的遗憾惋惜和不尽的怅惘回忆而告终的一幕,诗人在下节诗里以别开生面的浪漫之笔给我们作了一个充溢奇幻色彩、荡漾温馨情调的美妙回答。
时间移到了月光如洗的夜晚。桥上人和楼上人都带着各自的满足与缺憾回到了自己的休憩之所。可谁又能想到,在这一片静谧之中,白日里人们所作的感情上的投资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回报。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这不就是自然之景对桥上人白日里忘情于景的知遇之恩的热情回报吗?从“你”的那扇被“明月装饰了”的窗口上,我们可以想见到,此刻展现于桥上人眼际的会是一幅多么美丽迷人的月夜风光图啊!那桥、那水、那楼、那船、那柳……那窗外的一切一切都溶在这一片淡雅、轻柔、迷朦、缥缈的如织月色之中,与白日艳阳照耀下的一切相比,显得是那么神秘,那么奇妙,那么甜蜜,那么惬意。面对这月光下的美景,怎能让人相信自然之景是冷漠无情、不解人意的呢?怎能不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强烈钟爱呢?你爱自然,自然也会同样地爱你--这就是诗的理趣所在吧!
自然之景以其特有的方式回报了桥上人的多情,而桥上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楼上人的一片美意呢?诗以“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想象天外的神来之笔对此作了饶有情致的回答,从而使楼上人那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毫无希望的单恋之情得到了惬意的渲泄。
这个被“装饰”了的梦对于它的主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奥秘的深切剖白,它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那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压抑的单恋之情是多么地强烈灼人。而那桥上人之所以能由眼中人变为梦中人,不正因为他是意中人的缘故吗?诗里虽然没有一句爱情的直露表白,但这个玫瑰色的梦又把那没有表白的爱情表现得多么热烈、显豁,而由这个梦再来反思白日里的那一“看”,不是更觉得那质朴无华的一“看”缠裹了多少风情,又是多么激人遐思无尽吗?
如果仅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构图来表现单恋之情的奇妙迷人,那就显得太平庸一般,流于俗套了。诗的精妙新奇之处就在于,这个梦的主人不仅仅是梦的主角,而且还从这场爱情角逐的主动者位置上退居下来,而那个桥上人也已不再是毫无知觉的爱的承爱者,他是以主人的姿态在梦里扮演了一个爱的施予者的角色,他在尽其所能地“装饰”着这梦,而且,他也是在按着楼上人的心愿来“装饰”着这个梦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详尽地描绘出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梦境,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被“装饰”了的梦一定是无比甜蜜、无比美满、无比浪漫、无比美丽的。总之,楼上人那一片落花之意,终于得到了桥上人那流水之情的热烈的、远远超过希望值的丰盛回报。在这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句千百年来伴随人生长河,永远给人以惋惜、懊丧的格言也失去了它真理的意义。
但梦毕竟是梦,它代替不了现实;装饰也只是装饰,它总会露出虚幻的面目。当第二天红日高照,酣梦醒来,那楼上人“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时,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了呢?但相信,那已经尽情地领略了“落花若有意,流水亦含情”的甜蜜梦境的楼上人,定会从常人所有的那淡淡愁绪之中解脱出来,定会以更美好的憧憬,更深沉的爱心,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的。
当我们品评着这首小诗的不同凡响的题旨,流连于这首小诗的含蓄隽永的意境之中时,我们为什么还要作茧自缚,像诠释一道深奥的哲学命题那样去对它作枯燥乏味的理性分析呢?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多余的红补丁——《荷花淀》指瑕
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虽是已有定评的名篇佳作,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小说的第二、三、四节便属于可以删除而又不影响其全篇的赘笔。
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看,这两节可算作是小说的非情节因素,它中断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情节叙述,以向读者直白的形式,插入了作者对苇子多、席子好的白洋淀的赞美。虽然许多修辞书都把这两节作为典型范例,来讲解比喻、排比的妙处,但从写作学的角度看,这三节文字却恰似蓝衣服上的一块剌眼的红补丁,显得多余而累赘。
首先,这两节文字与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缺乏必然的有机联系。它既没有从宏观方面起到交代时代背景的作用(因为苇子多、席子好只是白洋淀古已有之的自然景观);也没有从微观方面为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提供具体的环境(水生嫂编席的具体环境在一、五节中已有了生动的描写:月亮、凉风、光洁如云的席……)。因而它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赘笔。
其次,从段落之间的衔接上看,第一节的末句“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与第五节的首句“这女人编着席”联结十分自然、紧密,而第二、三、四节突兀地插入“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的大段旁白,就既显得生硬勉强,人为割断了前后段的有机联系,又损害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柔美、安谧的氛围。如果删去了这三节,作品就显得浑然天成了。
再次,从作者写作的初衷看,他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而小说在总体风格上也确实给人一种纯客观叙述的真实感。但在第二、三、四节中,作者站出来向读者作直抒胸臆的旁白,则显然有违小说的这种“按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写实风格,成为整篇作品的一段不谐和的杂音。
最后,这三节文字的多余,还可以从有关这篇小说的研究材料中得到反证。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这篇小说的众多评论中,竟没有一段有关这三节文字的分析。(有篇专门分析《荷花淀》语言艺术的文章,拿前五段作例时,引文中恰恰省略了第二、三、四节)那么,对于这三节文字在小说中的作用,研究者是视而不见、略而不谈呢?还是因其多余累赘而为名家讳,就不得而知了。
《名作欣赏》1992年第4期
《文摘报》1992年9月20日转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错诗原是好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赏析
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浪迹丛谈》一书中,认定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的第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是错的。因为据史书记载,三峡猿只生长于南岸,北岸巫山山脉是南北走向,正迎着北方寒风,猿猴不宜生长,有人从南岸捉猿放到北岸,这猿最后还是跑回了南岸。于是,这位好事的学者据此理直气壮地将诗改成了“南岸猿声啼不住”,他自以为这样一改,诗才合乎情理,不至贻误后人。
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史书记载的正确,但“南岸猿声”的修改却并未因此而能迈进诗歌殿堂的门槛。个中原因倒不复杂,李白是诗人而不是科学家,李白作诗是要向人们抒发他那意外遇赦后的极度喜悦兴奋之情,而不是要向人们准确无误地介绍三峡猿的生长分布情况。把“南岸”写成“两岸”,虽不合理,但合情,虽是错诗,但是好诗。那么,从比较赏析的角度看,与“南岸猿声”相比,“两岸猿声”的妙处又在哪里呢?
其一,“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江流之急,船行之快,更能渲染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磅礴气势。试想,处在如此高速飞驰的轻舟上,穿行于七折八弯的航道中,诗人又怎么会分得清那若有若无的猿啼是在南岸还是在北岸呢?
其二,“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诗人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诗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如今遇赦得还,真恨不得一步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身在船中,心儿早就飞到了回归之地。心急火燎、迫不及待的诗人此时全神贯注于船行的前程,他又哪儿会格外留意猿啼之声来自何方呢?
其三,“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诗人意外遇赦后的喜悦畅快的心情。三峡猿啼,一向以凄切哀婉令人伤情著称,可如今在欣喜若狂的诗人听来,猿啼却是那样的轻盈悦耳,似乎猿猴为诗人的欢乐情绪所感染,竟然立于大江“两岸”,以如歌的猿啼来夹道欢送诗人归去。一个“两岸”,传神地渲染出了那欢送场面的热烈感人,而这一切不正是诗人那狂欢之心移情于物的结果吗?
其四,“两岸猿声”更富画意,更能激发起读者的艺术想象力。那猿声不绝于耳的郁郁苍苍的两岸崇山峻岭之间,一叶扁舟顺流飞驰而下,这不分明是一幅线条鲜明粗犷、气势阔大激越的大写意吗!如果改成“南岸”,这画面就会残缺不全,尽失匀称之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