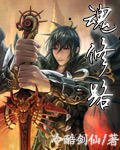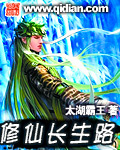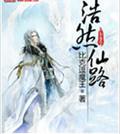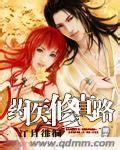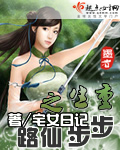朝圣的心路-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两种不同的梦。
第一种梦,它的内容是实际的,譬如说,梦想升官发财,梦想娶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或嫁一个富甲天下的款哥,梦想得诺贝尔奖金,等等。对于这些梦,弗洛伊德的定义是适用的:梦是未实现的愿望的替代。未实现不等于不可能实现,世上的确有人升了官发了财,娶了美人或嫁了富翁,得了诺贝尔奖金。这种梦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变成现实,如果不能,我们就说它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第二种梦,它的内容与实际无关,因而不能用能否变成现实来衡量它的价值。譬如说,陶渊明梦见桃花源,鲁迅梦见好的故事,但丁梦见天堂,或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梦见一片美丽的风景。这种梦不能实现也不需要实现,它的价值在其自身,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享受,而记载了这类梦的《桃花源记》、《好的故事》、《神曲》本身便成了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谓好梦成真往往是针对第一种梦发出的祝愿,我承认有其合理性。一则古代故事描绘了一个贫穷的樵夫,说他白天辛苦打柴,夜晚大做其富贵梦,奇异的是每晚的梦像连续剧一样向前推进,最后好像是当上了皇帝。这个樵夫因此过得十分快活,他的理由是:倘若把夜晚的梦当成现实,把白天的现实当成梦,他岂不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这种自欺的逻辑遭到了当时人的哄笑,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也多半会加入哄笑的行列。
可是,说到第二种梦,情形就很不同了。我想把这种梦的范围和含义扩大一些,举凡组成一个人的心灵生活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都可归入其中。这样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成真。但也不必在此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有着与第一种梦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不妨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好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真。对真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你不能说只有外在的荣华富贵是真实的,内在的智慧教养是虚假的。一个内心生活丰富的人,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把第一种梦称作物质的梦,把第二种梦称作精神的梦。不能说做第一种梦的人庸俗,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做物质的梦,从不做精神的梦,说他庸俗就不算冤枉。如果整个人类只梦见黄金而从不梦见天堂,则即使梦想成真,也只是生活在铺满金子的地狱里而已。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守望的距离》序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个散文集,汇集了我从1984年以来发表的几乎全部散文。尽管我出版过两个散文的单行本《只有一个人生》和《今天我活着》,即将出版一个散文的选本,但是仍然有许多想要购买我的作品的读者未能如愿,还有一些对我偏爱的读者希望得到完整的汇集,是他们促使我编了这个集子。
十余年的积累只是这么一本不厚的书,成果未免可怜。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写作的速度不快。我倒并没有“文章千古事”的觉悟和抱负,我的觉悟和抱负仅限于,写文章尽量做到有感而发,并且尽量减少(不可能避免)自我重复,于是难免下笔犹豫了。再说,我首先在生活,人生的变幻和命运的磨难每每使我无暇握笔。不过,同时我也发现,正是在变幻和磨难的极点,我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用真理和谎言救助自己。所以,如果把我的散文归入所谓闲适派,实在是误解。我毫不反对闲适,只是觉得自己离那境界还远。真正的闲适是自然无为,不需努力的,而我却是一个太执著的人,经过努力能达到的至多是超脱的境界罢了。
所谓超脱,并不是超然物外,遗世独立,而只是与自己在人世间的遭遇保持一个距离。有了这个距离,也就有了一种看世界的眼光。一个人一旦省悟人生的底蕴和限度,他在这个浮华世界上就很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了。不过,如果他对天下事仍有一份责任心,他在世上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合适的位置的,“守望者”便是为他定位的一个确切名称。我很喜欢这个名称,曾经想以此为刊名办一个杂志,可惜未能如愿。以我之见,“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恒的价值,望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曾经有一位读者来信,给我派了一个很好的差使:在激烈的竞技场上吹几声临时退场休息的哨子。做这种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扫兴,但还总有人会认为人生的使命不仅仅是竞争,也应包括休息和思考。那么,就让我为这些人好好吹哨吧。
《各自的朝圣路》序
托尔斯泰年老的时候,一个美国女作家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不写作了,托尔斯泰回答说:“这是无聊的事。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出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而应该行动。”
近来我好像也常常有这样的想法。看见人们正以可怕的速度写书、编书、造书、“策划”(这个词已经堂而皇之地上了版权页)书,每天有无数的新书涌入市场,叫卖声震耳欲聋,转眼间又都销声匿迹,我不禁想:我再往其中增加一本有什么意义吗?
可是,我还是往其中增加了一本。
我如此为自己解嘲:我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情做,活得有意义或者似乎有意义。所以,对于我来说,写作何尝不是一种行动呢。
托尔斯泰晚年之所以拒斥写作,是因为耻于智识界的虚伪,他决心与之划清界限,又愤于公众的麻木,他不愿再对爱慕虚荣的崇拜者说话。然而,事实上,托尔斯泰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他从前的文学创作也罢,后来的宣传宗教、上书沙皇、解放家奴、编写识字读本等所谓行动也罢,都是为了解决他自己灵魂的问题,是由不同的途径走向他心目中的那同一个上帝。正像罗曼?罗兰在驳斥所谓有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托尔斯泰的论调时所说的:“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我相信,这立场就是他对人生真理的不懈寻求,这关联就是他一直在走着的同一条朝圣路。
但我还是要庆幸托尔斯泰一生主要是用写作的方式来寻找和接近他的上帝的,我们因此才得以辨认他的朝圣的心迹。我想说的是,我要庆幸世上毕竟有真正的好书,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优秀灵魂的内在生活。不,不只是记录,当我读它们的时候,我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在写它们的同时就是在过一种真正的灵魂生活。这些书多半是沉默的,可是我知道它们存在着,等着我去把它们一本本打开,无论打开哪一本,都必定会是一次新的难忘的经历。读了这些书,我仿佛结识了一个个不同的朝圣者,他们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是的,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有多少条朝圣路。每一条朝圣的路都是每一个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不必相同,也不可能相同。然而,只要你自己也是一个朝圣者,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反而是一个鼓舞。你会发现,每个人正是靠自己的孤独的追求加入人类的精神传统的,而只要你的确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你其实并不孤独。
本书是我1996年至1998年所发表的文章的一个结集。东方出版社还曾出版过我此前文章的结集《守望的距离》,为了保持连续性,我把那个集子未及收进的1995年的部分文章也收在了本书中。我给这本书取现在这个名字,一是因为其中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几乎都是读了我所说的那些朝圣者的书而发的感想,二是因为我自己写作时心中悬着的对象常是隐藏在人群里的今日的朝圣者,不管世风如何浮躁,我始终读到他们存在的消息。当然,这个书名同时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鞭策,为我的写作立一标准。我对本书在总体上并不满意,但我还要努力。假如有一天写作真成了托尔斯泰所说的无聊的事,我就坚决搁笔,决不在这个文坛上瞎掺和下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1)
一
当我在1985年初写作那本论尼采的小册子时,我不曾料到,两年后会在中国出现一小阵子所谓“尼采热”。据我所知,真正对尼采思想发生共鸣,从中感受到一种发现的喜悦的,是一些关心人生问题、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生和青年艺术家。尼采思想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哲学表达,它之引起强烈共鸣,的确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危机心态。
这里我首先要为精神危机“正名”。人们常常把精神危机当做一个贬义词,一说哪里发生精神危机,似乎那里的社会和人已经*透顶。诚然,与健康相比,危机是病态。但是,与麻木相比,危机却显示了生机。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追求受挫,于是才有危机。如果时代生病了,一个人也许就只能在危机与麻木二者中作选择,只有那些优秀的灵魂才会对时代的疾病感到切肤之痛。
精神危机最严重的形态是信仰危机,即丧失了指导整个人生的根本信仰,一向被赋予最高价值的东西丧失了价值,人生失去了总体的意义和目标。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虚无主义。
这里所说的信仰,是指形而上意义上的信仰,即为人生设置一个终极的、绝对的根据,相信人的生命的某种永恒性和神圣性。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它的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历来缺少那种形而上和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只有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社会层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还限制了对人生终极根据的探究,掩盖了形而上层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会信仰一旦失去统摄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来了。这正是当今这一代青年所面临的情况。
无可否认,“*”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信仰失去了大一统的威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和“*”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是没有信仰的一代。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权威人生模式,每个人的命运都投入了未定之中,因而不得不从事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社会的商业化使人的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形既使有高贵精神趣味的人感到孤独,却也异常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追求的紧张度。
荣格曾区分“伪现代人”和“真正的现代人”,前者喜欢以现代人自命,后者则往往自称老古董。事实上,现代思潮的代表决非那些追求时髦的浅薄之辈,反倒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正像在任何一种信仰体制下,真正有信仰的人仅属少数一样,在任何一个发生精神危机的时代和民族,真正感受和保持着危机张力的也只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