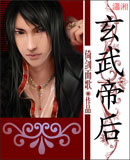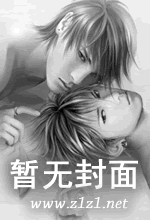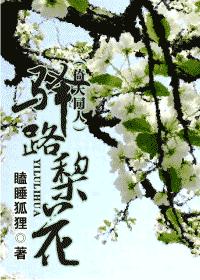迢递故园(倚天同人)-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浣与俞莲舟二人上得哨岗,凭栏向北远眺,但见远方一望无际平野千里。低垂野云将万物模糊在一派阴霾之中,天地之间一片秋末萧瑟之景,荒城故道外黄秃秃的泥泞地面上见不到半颗秋草,枯树枝桠扭曲纠结着。一只老鸦扑棱棱的落在上面,片刻寻不到食,“呱”的一声又挣扎着飞走了。
城根下传来的苍凉凄切的胡琴声,却是个老头子穿着件破得四处透风的棉袍,窝在墙根下咿咿呀呀的卖唱。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苍老的声音并不嘹亮,咿呀的胡琴声凄切催人心魄,在这样阴霾的天气里,随着瑟瑟秋风传得格外遥远。一句“百姓苦”如诉如怨,仿似叹息又仿似认命,竟是格外的清晰。沈浣远眺着北方得双眼微眯,深吸了一口气,昂起头闭上双眼,隔了良久方才微微的吐了出来。岗哨上的秋风益发的凉了,吹乱了她的发鬓,一时之间仿佛天地间只余下呜咽秋风应和着那苍凉胡琴。然而片刻后,她却听得俞莲舟低声道:“可要它?”
沈浣一地低头,却见俞莲舟修长的手掌摊开,手中一只笛子,通体光滑润泽,正是当初两人十里坡上分别之际她赠给他的那一支。乍见当年身边旧物,沈浣心中猛然一动,见得那笛子宛然如新,显然保存的极是妥帖,不由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但觉那笛身上犹自带着些温热,在这瑟瑟寒风中异常鲜明。
沈浣执起笛子,引宫按商,气息微吐,涤荡清冽之音蓦然鹊起,直上天际,凭乘了秋风,透彻了野云,正是那老者刚刚唱过的一曲《潼关怀古》。那笛音虽比不上胡琴特有的苍劲,却透出别样的荒凉,仿如暮色下的战场,带着摧人心魄纠结与寂寞。
整整晌午半日,俞莲舟与沈浣二人再没说过一句话,哨岗之上长风烈烈,笛音不绝。
--
阿瑜叹了口气,看着对面的俞莲舟,“总之,这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元虏就在那里,晚收拾几天也跑不了。可是大夫说了,元帅这旧伤若是不好好将养,祸患无穷。俞二侠,元帅这件事上最是不听人劝,你若有空便多劝她一劝,她最是敬你,你的话必是能入得她耳的。”沈浣与俞莲舟一回行营,当即命人召集所有校尉将官,点卯升帐。而阿瑜却拦下来俞莲舟。
俞莲舟微一沉吟,问道:“大夫如何说沈兄弟伤势?”
“这……”阿瑜顿住,颇是为难的看向俞莲舟道,“这俞二侠还是亲自去问元帅吧,我若说了,元帅不和我翻脸才怪。不过那大夫所诊倒是九成可信,他问也没问,一眼就断出元帅这伤已有六年,复发四次,可见诊断甚是可信。”
俞莲舟皱了双眉,半晌道:“沈兄弟师门那独门医治外伤的法子也是无用么?”
阿瑜一怔,睁大了眼,“医治外伤的独门法子?什么独门法子?”
她这一问把俞莲舟也问得愣住了,半晌没有动静。阿瑜忽地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她反应极快,脸上堆满笑意,“啊,俞二侠说的是那个……”谁承想她话音未落,但听得隔了十余丈的行营大帐之中忽然爆发出一声怒喝,紧接着一阵嘈杂的吵闹之声,伴随着东西落地碎裂的声音以及争执的声音。二人皆是心中一凛,俞莲舟脚下一点展开轻功越过两个营帐直奔大帐而去,阿瑜亦是拎起裙子跑了去。大帐门口,帐帘“噗啦”的一声被拉开,贺穹怒气冲冲的冲了出来,脸色通红恨意横生,一手倒提着兵刃,甩开大步腾腾走了几步,却被紧接着追出来的狄行一把拉住。贺穹似是恼极,被狄行这一拉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狠狠甩开他的手,怒道:“操他娘的别告诉老子你小子也同意退守!”
狄行被贺穹推开,又被这般一句喝骂,张口想说什么,但终究叹了一口气,闭口不言。贺穹见他被自己这一问问得哑口无言,不由得底气更足,高声向着那大帐喝骂道:“谁不知道你沈大元帅当年因为怕脱脱那条老狗,连帖木儿那娘货都不敢杀?!你沈大元帅怕这老狗,老子可他娘的不怕!老子这条贱命撂在这沙场上,也决计不能让元狗从咱这讨到半分便宜!到时候你沈大元帅尽管带着你的人马退守躲在这淮安城里,老子一个人去杀个痛快,就是被那老狗咬死,也不失一条汉子!”说着狠狠啐了一口,“呸!”
此时帐中亦有不少人出了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偏将以下的校尉们,各个噤若寒蝉。沈浣带兵这些年,却是头一次升帐时候,诸将之间闹成这般。
“贺大哥!”,楼羽几步上前按住贺穹,“元帅并非这般意思,贺大哥,话不可乱说!”
“呸!老子乱说?你他娘哪知耳朵听见老子乱说?”,贺穹瞪了楼羽一眼,指着大帐道:“避战是不是他说的?退守是不是他说的?他娘的避战个屁,退守个屁!你干嘛不干脆降了脱脱那老狗?去舔他臭鞋?!”
“贺大哥!”楼羽赶紧一拉贺穹,“这不只是同我等商议呢么?也没说立时便要退。”
狄行却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此时脱脱若是过得淮安,大江以南再少有险阻可守,归德淮安二路千里沃野可是尽归元军了。”
周召此时也出了来,冲几人摇摇头,“元帅说得也不无道理,黄淮几路行省大灾,此时用兵,必是两败俱伤。”
楼羽劝道:“无论如何,先回帐吧。都是兄弟,何事不好商量?”
贺穹一甩手,“商量个屁!老子一听退守就恨不得现在杀将出去!你沈大元帅看着那四十万大军就怕了?要撤了?你就不觉得你那手中的沥泉枪烫手么?!你就不怕三更半夜里岳公来教训你这不肖传人么?!沥泉枪?狗屁沥泉枪!岳公他瞎了眼,这枪才落到你手里糟蹋!”
他这话一出,狄行、楼羽、周召几乎同时喝出声:“贺大哥!”
正值此时,大帐帐帘一掀,先是方齐出了来,随即沈浣抬手一撩,亦是出了来,身侧站着戴思秦。大帐外面,五六个将领三十多个校尉校尉同时看向沈浣,不解者有之,迷茫者有之,愤满者有之。沈浣抬首,缓缓扫视了每个人一眼,在贺穹的脸上停留片刻,微微叹了口气,一挥手道:“今日散帐吧,明日再议。”
诸人听得此言,神情各异,皆是躬身行礼,随即散了去。
待得诸将去得远了,沈浣身后的戴思秦上前一步,“元帅。”
沈浣看了他一眼,“怎么,思秦你也不同意避战退守?”
戴思秦却是摇头道:“不然。《孙子九地》中有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给,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元帅,以思秦浅见,当下淮安无粮无草,又新受灾,脱脱势必乘我不给,攻我不戒,是以此地绝非与脱脱四十万大军一决高下之地。”
沈浣长舒一口气。方才她提出避开脱脱四十万大军锋芒,避而不战,几乎所有战将均是心中不虞。贺穹是粗豪性子,当场大骂,便是狄行楼羽等老将,虽然嘴上不说,心中却是不乐意的,此时唯有戴思秦一人如此说。沈浣拍了拍戴思秦的肩,半晌道:“你也去吧,让我再考虑一番。”
戴思秦躬身行礼,刚要离去,忽地想起什么,向沈浣道:“元帅,贺将军一家八年前都死在脱脱手里。他八旬老母甚至被腰斩弃市,今日他出言不逊,实是情有可原,您莫要同他计较。”
沈浣点了点头,轻声道:“我自是晓得,你且放心,决计不会的。”
戴思秦松了口气,又向沈浣拱了拱手,随即一敛前襟便去了。
帐前三十余人很快散得干净,片刻间只剩下沈浣,阿瑜与俞莲舟三人。阿瑜似是想起什么,一路小跑往厨房去了。
沈浣隔着两三丈距离,看向俞莲舟,面上苦笑,心口仿如梗了一块石头一般,硌着磨着心头血肉,隐隐生疼。
俞莲舟却并不多看她,只走上前,却又越过她,往后面校场而去,留下一句:“可要再比试一番?”
--
天色已是薄暮时分,晚风清寒,瑟瑟刮过偌大无人的校场之上。俞莲舟盘膝闭目坐在场边高台之上,微睁开眼,却见沈浣一柄沥泉枪上下翻飞疾若惊雷矫若游龙,招式由古朴狠辣而至气势磅礴,惊起满场飞沙走石。
方才沈浣与他在校场之上一番比试,沈浣用枪他用剑,相斗五百余招。其后他一跃退出战圈,沈浣却是不曾停下,一柄沥泉大开大合,独自一人在场上练起枪来。接连一个时辰,招式竟无一招重复。俞莲舟却是坐在场边,也不去看她,兀自打坐用起功来。
又不知过了几许,沈浣一声清啸,长枪一回一转抛手而起直冲天际,她脚下一点,冲天直追那长枪而去,于半空之中一手钩住枪尾,倒翻一个身,长枪犹如九天惊雷,只听的“哐当”一声,校场边一根人腰粗的柱子应声由柱心碎裂开来,七七八八散落一地。
沈浣看也不看那柱子,默然立在场边,急速喘息不已。先是同俞莲舟激斗五百余招,随即又招招满力的练了将近两个时辰的枪,内力再好也已撑将不住。此时方一静下来,沈浣但觉周身四处都已被汗水浸透。她抹去额上汗水,提了沥泉,向俞莲舟走来。俞莲舟并不睁眼,任她在自己身边坐下。过得半晌,沈浣喘息渐平,俞莲舟缓缓吐出一口气,收了功,侧头看了沈浣一眼,听得她喃喃低声道:“我应过师兄,决不让北方元军渡过淮水半步。”说着神情涩然,“千金一诺……千金一诺……”
俞莲舟忽而肃声道:“兵法,我所知寥寥。但是今日,只凭你心中所想,便配得上这沥泉枪。”
言罢他拍了拍沈浣肩头,沈浣微微一窒,嘴角忽而勾起三分,低头去看手中长枪,但见初上星辉映着其青泓枪刃,犹若流光,映亮了她的眼。
--
至元五年,黄淮暴雨,田舆皆没,难者十万余。
是岁,桃园、淮安、清泗大饥,粮价十倍于常时。
山野草木无不取之为食,路曝山秃,饿殍遍野。岁末,以尸为食者遍矣。
第五十九章 何人得与此心同
“淮安一役,颍州军困守城池一月又三日,实非智举。为将者,当善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己所用。彼时城北黄淮水位暴涨,城内河防高筑,而冬之将至,元军必急于渡河扎营。可诱敌深入城内,待得元军尽数入城,关闭四门,于城北提闸放水,则四十万元军不复存矣。何如困守三十三日余,备受诟病,复又战于高邮?错尽天时,徒费地利,自毁人和,实非将者所为。”
二十年后,萧策读罢自己徒弟论述当初至元五年末高淮之战的策论,看了看座下正略有紧张看着自己神情的少年,轻轻放下手中文章,笑道:“不错,天时地利人和之道,你已明白得差不多了。能写出这借黄淮秋汛水淹淮安,不费一兵一卒剿灭对方四十万大军,可见你已是得了法家精髓。”
少年脸上神情一喜,却听得萧策忽而话锋一转,“可你认为,你师娘当初作为颍州军主帅,又可懂这一点么?”
少年被问得蓦然一愣,立时脱口道:“懂!”这几年他在萧策座下研习兵法,萧策给他所读的例多,颇有不少便是沈浣当年带兵之时的战计兵法。几乎每读一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