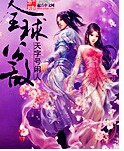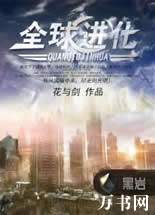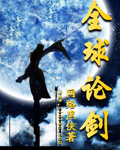全球通史(下册)-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reed和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圆脸”、“丝柏状身材”和“鲜红鱼嘴唇”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夜莺”给提到了,“玫瑰花”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除这些主要的文化活动领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绘细密画、编织地毯和纺织品、烧制瓷器、鞣制皮革和制作珠宝饰物等方面。
四、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突然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落后。
一个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1566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里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然而,他的腐化堕落还不如他以后的许多可耻的继任者那么严重。这一时期,有位奥斯曼帝国的朝臣曾写道,易卜拉欣一世于1649年成为苏丹后,便“落入后宫的亲信和同伴、侏儒、哑巴、宦官及女人们的手中……他们一道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这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波斯;在波斯,阿拔斯的继承人于1629年登上王位后,也受制于后宫的影响。
在印度,帝国的衰落始于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执政时。奥朗则布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出色的行政官和一位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缺点:不能容忍其印度教臣民,尤其是在他漫长统治的后半阶段。他将阿克巴制定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视作恰恰是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否定。1669年,他下令“废除异教徒的所有庙宇和学校。”10年后,他又向印度教徒重行征收一世纪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头税。奥朗则布还尽可能完全地把印度教徒赶出军队和官僚机构。这种种歧视手段自然引起广大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抗。战争爆发了,并延续到固执的奥朗则布91岁去世时。奥朗则布把印度留在紧张、虚竭的状态中,而他的后继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家伙,根本无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曾产生过杰出的巴布尔、阿克巴和同样杰出然而误入歧途的奥朗则布的王朝,此时又出现了“无头脑者”巴哈都尔沙和“快活人”即“贪图享乐者”穆罕默德沙。所以,18世纪,随着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进犯以及欧洲人窃据沿海立足点,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这种王朝的腐败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尤为严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本人之手。土耳其谚语道:“鱼烂头先臭。”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国家遭摧毁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王室都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对于穆斯杯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较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的动力。它未经历过前章所提到的、这些世纪中正在使欧洲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变化。
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农业、工业、金融方法或商业组织,均末发生根本变化。如果17、18世纪中,有位旅行者进入穆斯林国家,那他一定会看到早500年时十字军战士已目睹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事实上,17世纪末,有位英国人确访问过君士坦丁堡;他对那里的萧条和衰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
在君士坦丁堡,假如哪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需要合身的衣服,需要布置房间用的家具,需要可供学习、消遣的书籍或地图,需要纸、笔、墨水、餐具、鞋、帽子,总之,需要那些几乎在世界各城市都可找到的物品,那么,他将会发现,除了一些质量极为低劣、叫人都弄不清可派什么用场的物品外,几乎啥也没有。摆出来待售的少数商品;要么是英国的、不适宜其他任何市场的出口货,要么更糟,是德意志和荷兰仿效英国造的仿制品。……假如哪位外国人丢逛集市,他能见到的只不过是拖鞋、用烂皮革制的粗陋的长筒靴、粗劣的棉布、烟斗、烟草、咖啡、餐馆、药材、花卉、旧手枪、短剑以及世上最差的制成品。……如果从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如果细察其内部,它的惨状和缺陷教人触目惊心,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贫困的都城。
以上引文的作者即那位旅行者,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还下了这样一句评语:“要是隶属英明的政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说不定会得到地球上所有商国的财富。”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与穆斯林帝国政府的腐败密切相关,是无可置疑的。正如巴斯比卡所说的,只要统治者精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绪起来,诈欺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人管束得了,扼制了私营企业和对个人富有激发力的因素。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为肆意搜刮者的攻击对象。因此,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而不公开进行投资,以扩大自己的买卖。这一点已一再明确地为外国观察者所证实。例如:17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呆了几年,他写道:
农民、工匠或商人受了伤害,却找不到一个能倾听自己诉苦的对象;象法国那种能制止残忍的压迫者“总督、封建主和税吏”胡作非为的杰出的君主、议会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能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暴君手执权柄。老在伺机攫取任何人辛勤劳动的果实。假如有谁得到财产……他的生活决不会过得比以前舒适,他也决不可摆出付生活优裕自在的样子,相反,他须琢磨装穷的办法:衣着、住所和家具得依然简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终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饮食之乐。同时,他的金银钱财还须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农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暴君也许明天就会来,用贪婪的手夺去我所拥有并看重的一切,连能使我的悲惨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东西……也不留下,我干吗要为一个暴君卖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实,足以说明亚洲国家迅速衰落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政体,在印度斯坦,大多数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质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镇,只要不是已经毁灭和遭到遗弃的。都具有行将衰微的明显标志。
得出这些结论的,并不只是外国观察者。有位叫约翰·普里戈斯的希腊商人,离开受土耳其人统治的祖国后,在阿姆斯特丹发了队在那座城市里,人们能够平安、公平地做商业买卖;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过一番很能说明情况的抱怨的话:
但是、在土耳其人统治下,谁也无法生活。土耳其人不讲秩序,也不讲公道。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让它增加10倍,结果,他们去劫掠其他人,让其他人受穷,他们不明白,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他们是完全不讲公道的,而且,他们什么都创造不了,只会搞破坏。愿上帝把他们毁了,使希腊能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能占上风,使政府能象左欧洲那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沙漠滩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是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1500年时便已达到这一境地。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立时,还得到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理解的;在18世纪,则是荒唐的、自取灭亡的。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不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他们自己那时什么也没做,也不打算将来做些什么。
这种无知和唯我独尊不能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据传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将伊斯兰教与思想发展的停滞相提并论。所以,穆斯林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该到伊斯兰教的信条中去找,而应用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奄奄一息的状况来解释。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已没落到它只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的程度。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而这种研究颇为肤浅,只是以琐细无意义的分析为主要方法。
关于这一点,伯尼埃的观察报告和绘论特别有价值。伯尼埃曾受业于法国著名科学家皮尔·伽桑狄,是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后来,1656至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东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认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毫无成效,一方面是因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极其缺乏从事实验性的、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或愿望。他写道:
普遍、极度的无知是我所努力描绘的那种社会状态的必然结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适当地捐赠基金,难道就能创办起专科学校和学院?我们上哪儿去找创办人?或者,就开院校建立了,上哪儿去聘学者?其财力足以资助子女上学的人又在哪儿?或者,就算有这样的人,谁又敢于露出如此明白的证据表明自己很富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