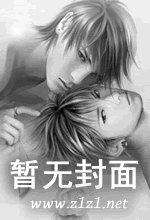补天裂-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若翰差不多同时来华的,他们因为译书、办报有功,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分别被授予三品和五品官衔,林若翰至今仍然是一名布衣白丁,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继。他急于建功立业,却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押”错了“宝”,变法失败,翻云覆雨,他不但一无所获,还交恶于皇太后及其“后党”,成为在北京不受欢迎的人,从此结束了在中国的政治生涯,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中国问题专家”痛失用武之地!这一惨败使他对政治心灰意冷,返回香港,退隐翰园,不求闻达,只愿主赐给他平安,在爱女的陪伴下度过余生。然而他又怎能料到,向来毫无瓜葛的迟孟桓却在这时把手伸进翰园,打破了这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平地骤起波澜,使他在一怒之下大病罹身,险些提前去见上帝!就在他头脑昏昏、心烦意乱地卧病在床之际,魔鬼让他犯了又一个错误:谢绝出席总督宣誓就职典礼。为什么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试想,如果在北京的时候接到光绪皇帝召见的谕令,即使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他会谢绝吗?当然不会,哪怕是他所不喜欢的皇太后,假若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传下懿旨让他到颐和园陛见,他也会受宠若惊,抱病驰驱,三跪九叩,谢主隆恩。那么,为什么对卜力总督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你毕竟不是大清国的臣民,北京之行成也罢,败也罢,可留则留,当去则去,哪怕一辈子不再涉足中国大陆,总还是另有天地;可是,你是一名英国公民啊,居住香港三十八年之久,应该比谁都明白,总督是奉大英女王陛下之命统治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这块远东殖民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甚至说“总督仅次于上帝”,而你是居住在香港的大英臣民,对你来说,难道总督不比中国皇帝、皇太后更重要吗?新总督宣誓就职是香港的头等大事,许多人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够亲身恭临盛典,而你接到了请柬却自动放弃了。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狂妄之极!你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圣约翰大教堂的牧师,在宗教崇拜典礼中你是主角,充当上帝的代言人,为信徒所仰望,而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总督才是主角,你连个小小的配角都不是,只不过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是总督治下的一个老百姓而已,有什么可狂妄啊?不,上帝可以作证,林若翰虽然有些孤傲自负,但并不是一个目无尊长的人,更不可能连总督都不放在眼里,居住香港三十八年来,他先后经历了赫科莱斯·罗便臣、麦当奴、坚尼地、轩尼诗、宝云、德辅、威廉·罗便臣时代,已经是“七朝元老”,七位总督照例都是到圣约翰大教堂参加各种崇拜仪式,林若翰历来对他们都是恭而敬之,怎么可能惟独对新官上任的卜力总督大不敬呢?实在是因为重病之中心力交瘁而疏忽了!他以为只要据实禀报自己正在生病,便可以得到谅解,岂不知,怀疑和猜忌是人的天性,你所说的话别人就都相信吗?那么重要的场合你不出席,就给了别人任意猜测的权利,人家说什么是什么,“人言可畏”啊!而总督刚刚到任,人地生疏,必然先入为主,对这个谢绝出席他的就职庆典的人还能有什么好印象?在总督的五年任期之内,圣约翰大教堂是他参加主日崇拜必到的地方,今天刚刚是第一次,就已经让林若翰领受了这份尴尬,未来漫长的五年又该怎么度过?
想到这些,老牧师懊悔不已,口中诵读的《认罪文》字字句句打在他的心上,“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反倒去做”,是啊,自己为什么犯下了这样的过错,得罪了总督呢?“现在我们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求主怜悯、赦免”,也许在上帝眼中,这样的疏忽并不算犯罪,可以赦免,但谁知道总督肯不肯赦免他?现在,“仅次于上帝”的总督就在他的面前,那副毫无表情的面孔,那双凌厉的眼睛,高深莫测,令人望而生畏!
涔涔冷汗渗出林若翰的额头,一颗心像悬浮在空中的气球,飘飘忽忽没有着落……
翰园的客房里,易君恕正在伏案命笔,书写教材。他为倚阑小姐授课并没有一部现成的教材,而是从翰翁的大量藏书中找几本唐诗、宋词的选本,根据倚阑的接受能力,从中选出一些篇幅短小、文字浅易而又内容与文采俱佳、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篇,向她进行最为基本的汉文教育。易君恕每天晚上把预定的篇目书写出来,次日教她诵读,详细讲解,课后再让她抄写、背诵,下次上课之前,还要先把上一课“回讲”,以考察她领悟的程度。
前天,倚阑小姐为了接待迟孟桓而停课,使易君恕非常恼火,他打算向翰翁提出:中止这项授课计划,不教了!但是,翰翁的突然发病打乱了翰园的一切,他不忍在这个时候再刺激老人了。翰翁病愈之后,翰园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倚阑小姐的汉语课还得继续上。此刻,易君恕正在书房里写明天的教材,这是文天祥的那首著名的七言律诗《过零丁洋》,连标题不过六十个字,却是字字重若千钧,令人觉得笔端沉甸甸的。易君恕以工整秀挺的小楷书写完毕,仔细校阅一遍,并无脱漏错讹,便放在一边,拿过放在旁边的当日报纸,逐页翻阅。
香港不像北京那样只有一份黄皮《京报》,这里的报纸每天一大摞,英文报纸《德臣西报》、《士蔑西报》、《孖刺西报》,易君恕看不懂,但翰园也订了几份汉文报纸《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就成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每日必读,从中搜寻来自中国大陆的信息。近几天来,新任港督卜力爵士当然是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大幅照片连日占据各报的头版头条,还有连篇累牍的文章,详细报道总督的种种活动,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甚至迅速地了解到卜力昔日在英国殖民地巴哈马、纽芬兰、牙买加担任总督期间的大量“政绩”,及时地奉告于香港市民,此举当然也将博得新总督对报馆的青睐。更有专写“花边新闻”的无聊文人,深谙英国人“爱我便爱我的狗”的独特心理,对卜力上任时带来的那只狼狗也跟踪报道,将总督爱犬“盖瑞”的玉照刊登于报端,并且大肆吹捧,恰恰戊戌年是狗年,还没过去,便借题发挥,称“灵犬自西方来,为本港犬年增瑞”云云,读之令人作呕。
“文人堕落到这等地步,真是斯文扫地!”易君恕嗤之以鼻,无心再看了,便丢开报纸,从写字台前站起身来,想去门房问一问阿宽,今天有没有他的信。其实,每天早晨邮差一到,阿宽立即把报纸和信件送上楼来,从不耽误。林若翰在英国、在香港都有许多朋友,倚阑小姐也有一些昔日的同学,还有一些教友慕名向林牧师请教,翰园几乎每天都有信来,那些英文信件、阿宽一望而知与易先生没有关系,便呈送牧师和小姐,还从来没有一封信是寄给易先生的。每天阿宽托着报纸和信件一上楼,易君恕迎头便问:“阿宽,有我的信吗?”阿宽总是遗憾地说:“没有,先生。”看着他那惘然若失的样子,就再宽慰他几句:“先生,不要着急,北京到香港这么远,信到得不及时也是难免的,再耐心地等一等。只要你的信一到,我马上给你送来!”易君恕完全相信,只要阿宽见到北京来信,一定会兴奋地跑上楼,急切地喊着:“易先生,你的信!”今天,阿宽已经来过了,只送来报纸,没有信。但是,易君恕仍然忍不住再去问一问,让阿宽仔细查一查,万一他刚才看得不仔细,遗落在门房呢?疏忽人人会有的,这也说不定!
易君恕步出房间,下了楼,往院子里走去。
院子里空无一人,比往日更安静。易君恕有些奇怪,平时只要从窗口往外看一眼,就会看见阿宽在莳花弄草,忙个不停,今天怎不见阿宽的身影呢?
他沿着鹅卵石甬路走到院子的尽头,来到门房跟前,见那扇门关着,阿宽肯定是在屋里。便抬起手来,正要推门,喊一声:“阿宽!”却突然想到今天是星期日,牧师和小姐都去了教堂,阿宽难得休息一天,也许现在正在睡觉,便不忍心打扰他,缩回了手,即将出口的那一声喊也咽住了。
此时却听见屋里传出阿宽说话的声音:“你早该来,十四年了,我可真想你啊!天天盼望能梦见你,可总是见不着,今天总算把你盼来了!……”
那声音不高,却极其真挚,极其恳切,好像是久别的故人重逢,在促膝叙旧。易君恕心中一动:不知阿宽在和什么人说话?平日只觉得他无家无室,年近五十仍孤身一人,以翰园为家,栖身于这间小小的门房,也令人同情,可是阿宽毕竟还有人来往,比起我这举目无亲,倒还要强些呢!
他心中感叹着,转过身,正要原路返回,又听阿宽在屋里说道:“你可别走啊!坐下,就坐在这里,我有话要跟你说!兄弟,我现在遇到了难处,前面横着一道关,怕是过不去了,你可得帮帮我啊!……”
易君恕虽然站在门外,看不见屋里的情形,但从那悲悲切切的声音听得出,此刻的阿宽已是声泪俱下,正在哀哀地向人求助!易君恕不禁吃了一惊:阿宽遇到了难处?他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跟翰翁讲,倒求外面的人帮助!我自从来到翰园,事无巨细都得到阿宽的照应,如今他有难处,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这么一想,心裹着急,便伸手去推门,叫声:“阿宽!”
门“呀”地一声被推开了,易君恕倒愣住了!这间小小的门房,一览无余,除了阿宽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阿宽正跪在地上,面前摆着一把空空的木椅,椅子前面的砖地上有一堆纸灰,里面还有一两片还没有燃尽的纸钱……
“啊?易先生!”阿宽突然看见他进来,大惊失色,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他,嘴唇哆哆嗦嗦,一时手足无措……
“噢,对不起,阿宽!”易君恕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刚才听见你在说话……”
“啊!你听见了?”阿宽慌乱地从地上站起来,一把把他拉进来,关上了门,插上了闩,急切地问他,“易先生,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我……我是来问问有没有我的信,无意中听见的,”易君恕很觉尴尬,解释说,“也没有听清楚,好像你是在求什么人帮助,我怕你出了事,所以就……唉,我哪知道你是在自言自语!你这是在祭奠亡人吧?”
“哦,是啊,是啊……”阿宽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抬起衣袖擦了一把泪,说,“是祭奠我的兄弟,他死了十四年了!往年每到阴历十月初一,我都要出去给他烧些纸钱,‘十月一,鬼穿衣’嘛,他死的时候光着脊梁,得给他送点钱,添件衣裳。这些天翰园的事情忙,十月初一都过了,我还没给他送钱去,对不起亡人哪!我刚才恍恍惚惚地觉得他找我来了,这不,赶紧给他补上……”
“噢……”易君恕点点头,他也知道,像亡人托梦之类的说法固然不足为信,无非是活人对亡人思念之深,心有所感罢了,但阿宽的这种手足之情却令人感动,便问道,“你的那位兄弟是怎么死的?”
“唉!”阿宽长叹一声,声音哽咽了,泪珠滴滴嗒嗒地往下掉,“我的阿炜兄弟,他可死得惨啊!……”
圣约翰大教堂里,庄严的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