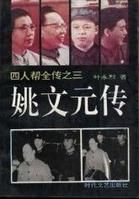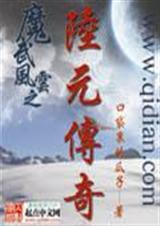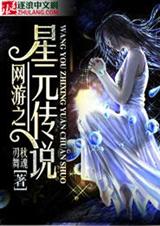姚文元传-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总算乌纱帽还在。
回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二月十八日匆匆飞回上海。
二月二十三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象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象地火在上海滩下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都。
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了一个书记。
紧接着,江青顺风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
顿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党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而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倒被毛泽东说中了:“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
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的王力有两个。一个王力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潜心于学术研究,“龙虫并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诣甚深的学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难逃,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批斗。
“中央文革”的王力,则是另一个。此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解放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六十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九月,为了纪念抗日胜利二十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比姚文元大十二岁,是四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一九一九年七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一九三三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起改名关锋。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九四七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五○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一九五二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五五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一九六二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成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市人,比姚文元小一岁,是四个“秀才”中最年轻的一个。跟姚文元一样,是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一九六二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挨整的八个“司马”,都是年轻干部,其中之一便是成本禹。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成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回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起挑战,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就在成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毕,气愤地对家人说道:“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