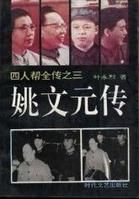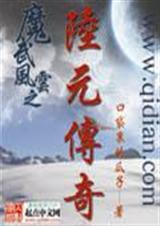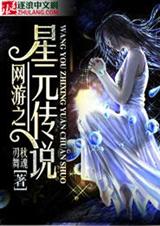姚文元传-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漠当年的激扬文字,望文生义,歪批“骆漠”。
那天罗竹风从华侨饭店开完杂文座谈会,回到家中,细思量,却觉得姚文元命题的《敲锣说》难以落笔,无法成文。
数日后,潇潇春雨,绵绵不绝。住在六楼的罗竹风,望着低垂着的铅灰色云层,仿佛天也矮了半截。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细雨不时飘洒在脸上,倒觉得头脑清醒得多。
“笃,笃笃……”响起敲门声。
妻前去开门。来者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黑布伞,腋下夹着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来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勋,老编辑也。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续西行漫记》,也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自一九二七年起,便献身于编辑工作。一九三八年,他担任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他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一个局长,一个社长,闲聊也离不了本行,谈起了编辑的苦经,编辑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光在会上“出气”,在会外也“出气”!
蒯斯曛给罗竹风送来了“灵感”。
当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飘飘洒洒的牛毛细雨之中,罗竹风乘着电梯,回到了六楼家中。他站在窗边,望着绵绵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宽大的写字桌旁,挥笔疾书。于是,稿纸上便出现了一行标题:《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他作为出版局代局长,感到写上真名实姓诸多不便——这篇短文会被读者看成是局长的呼吁。于是,他写上了他过去用过的笔名“骆漠”。
写罢短文,他提笔给多次前来约稿的《文汇报》女编辑余仙藻挥就一函:
“仙藻同志:
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引起了写作的冲动,草成《杂家》一稿,请阅处。
罗竹风“
《杂家》一文很快就在《文汇报》上披露。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千把字的短文会惹出一桩“《杂家》事件”。在“文革”中,责任编辑余仙藻因此被没收了记者证;为《杂家》写了《编后记》的《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多次检讨,如他自己所言“屁股都给打烂”;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斗台;对《杂家》一文表示过赞同的几十个人,受到株连……
迄今,仍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关于《杂家》的寒光闪闪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问,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引者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抛出一篇反党杂文《杂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写文章予以回击。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庆施同志几次在会上点名批判了反党分子罗竹风。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也明确指出:《杂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指向党的。可是陈其五呢,他一面勾结党内党外的反动‘权威’和黑线、黑网人物,对姚文元同志进行反革命围攻;一面拼命给这个反党分子鼓气:‘老罗,我是支持你的。’同时还赤膊上阵,专门找姚文元同志谈话,对他施加政治压力。正是在陈其五之流的策动下,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一小摄走资派及其爪牙、亲信,纷纷行动起来。文艺黑网上的小爬虫刘金,就更为活跃,赶写了一篇黑文给报社,恶毒咒骂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贼心虚,还加了注解,说是‘文章估计不会用,但一吐为快’。请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仇恨啊!他们把无情地批判他们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铁扫帚’。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这篇以“造反派”口气写的文章,把话说得明白不过了:原来,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着强大的后台——“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的柯庆施和张春桥,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随着《杂家》挨棍,很快的,刚刚复苏的杂文之花,又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
“大写十三年”的吹鼓手
巴金、熊佛西、丁伶、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上海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聚集在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那是二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元旦联欢会在那里举行。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地变得“重要”起来?
一月六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柯庆施说: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的讲话,概括为一个崭新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一月六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你一点,我一条,在张春桥的家里,姚文元跟张春桥拼凑着“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象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
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调的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来,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笔伸进音乐领域。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岁的他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写了篇《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在“读者中来”登出。这一回,大不一样,三十二岁的他,把“金棍子”伸进了陌生的“音乐王国”。
文章一开头,诚如他的“美学笔记”一样,先来一番谦谦之词:
“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说来的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乐名著’,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于是就去看编辑部所写的‘内容提要’…”
虽然姚文元自己承认对德彪西“一无所知”,对音乐理论“十分陌生”,即使随手“翻翻”那本小册子,也因“文章极其费解”而“咬紧牙关读下去”——姚文元并未读懂,却抡起棍子打了起来,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书的编者们。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