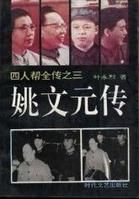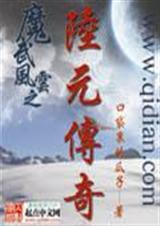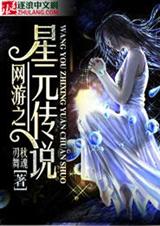姚文元传-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林荫夹道,同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二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九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九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象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个破了边沿的搪瓷碗,里头有几颗淡黄色的棕子糖。处处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觉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有点“资产阶级”气味,使用“赤膊”的棕子糖招待客人,象征着“无产阶级”的“风格”。
姚文元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棕子精,放进嘴里。虽说这么一来他讲话更不顺畅了,但是棕子糖的甜丝丝的感觉,使他不象刚才那么拘谨了。
姚文元提及了父亲是“鲁迅的战友”,本意是借此引起这位张总编对自己的重视,想说明自己并非一般通讯员,而是出自“书香门第”、“作家之家”的“新苗”。张春桥确实因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这才看中了他。不过,张春桥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姚文元一派“左”言,显然是做“棍子”的好料子。不过,要找几个这样的青年并不难。张春桥所需要的是“听话”的“棍子”。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文坛的张春阶,当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张春桥很喜欢那些有着“小辫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听计从……
若干年后,当姚文元成为张春桥手下颇有名气的“根子”时,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张春桥忽然讲起了“它蚂蚁政策”。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说道:“白蚂蚁会从内部蛀空大厦,这是谁都知道的。国民党居然从白蚂蚁身上得到启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政策,本来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后来,改变了政策,诱逼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叛变,再放回去。这些叛徒就成了白蚂蚁,从内部蛀空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蚂蚁政策’,是从姚蓬子开始的……”
讲到这里,张春桥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只见姚文元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
后来,姚文元即便因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名震全国”,即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始终对张春桥俯首贴耳,成为张春桥的“亲密战友”。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那天,张春桥言语不多。留在姚文元脑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理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政治家。要随时随刻注意政治风云的变化。我这儿消息灵通。有空,过来坐坐……”
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破天荒,一辆小轿车停在中共卢湾区委门口,说是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社开批判胡风座谈会。
姚文元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宣传部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姚文元的大名赫然印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而是整整一大版。那文章的标题,显得颇有气派,十足的“革命”味儿:《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
这是姚文元从发表“处女作”以来,惨淡经营了六年之久,第一次发表的“有分量”的文章。
当天晚上九点多,姚文元就来到张春桥家里,说了一番出自心底的感激的话。确确实实,没有张总编的支持,当时的无名小卒怎能在堂堂的《解放日报》上打响这一炮?
“吃,吃,吃粽子糖。”张春桥又一次端出了搪瓷碗。
“粽子糖真好吃。”姚文元又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粽子糖,塞进了嘴巴。
“跟胡风的斗争,还会‘升级’。”张春桥吞云吐雾,透过袅袅青烟,把重要的动向告诉了姚文元,“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央会有新的部署。在上海,敢碰胡风的人不多,尤其是硬碰、真碰的人不多。你还可以给《解放日报》写几篇!”
铭心刻骨,姚文元感激张春桥的“栽培”。
张春桥果真对来自中央的消息非常灵通。经过他的亲自安排,姚文元以反胡风的“英雄”的姿态,在五月份的《解放日报》上出现了:
五月七日,刊出姚文元的《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
五月九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
五月十一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
如此隔日一篇,姚文元名声大振。
最令人震惊的是,不早不晚,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以几整版的篇幅,刊出关于胡风等人的第一批材料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所写的那著名的《编者按语》。批判胡风,不再是学术性的批判,而是提高到“反党集团”(自六月十日起改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
多亏张春桥提供了重要信息,姚文元能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的前夕,抢先抛出三篇批判文章,戴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
紧接着,五月十七日,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登出《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那是“看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胡风反党活动的材料”,姚文元“感到愤怒”,于当天深夜赶写此文。姚文元写道:“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更可以看到一个极端黑暗极端无耻的灵魂,一个被狂热的唯心主义和最下贱的政客手段所养育着的丑恶的灵魂……”
姚文元对胡风泼尽污水,最后,发出如此“誓言”:“我表示:我要尽一切力量继续投入斗争,我也希望进一步动员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的罪恶行为,两面派恶劣手腕,给以十倍的还击。”
一星期后,《人民日报》登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同时刊出毛泽东写的《驳“舆论一律”》。
又过了一星期,六月一日,姚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的文章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这篇文章是经张春桥审定、推荐,而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当《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张春桥当即嘱令《解放日报》于六月三日转载。
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的调子唱得更高了: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目的,他们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和使反革命政权复辟的阴谋,现在是赤裸裸完全暴露出来了。……
“我要求把胡风反党集团全部阴谋活动彻底追查清楚。
“我要求对党的死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胡风依法予以惩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姚文元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他发表了十三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半数登在《解放日报》上。他作为“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于是乎,他给自己插上了一根美丽的羽毛,曰:“青年文艺理论家”!他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就这样,姚文元靠着批胡风起家,靠着张春桥往上爬。他所写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竟奇迹般变为他批胡风的“资本”。
从此,他把见风使舵当成看家本领。把“反戈一击”当作“成功秘诀”。他成为文坛上的投机商。
跌入了泥泞的路
反胡风运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达到了高潮: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二十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
照理,作为反胡风的“英雄”的姚文元,此时此际应当然鼓噪而进,再发表一批讨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从报刊上消失了:从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连“豆腐干”文章也未曾发过一篇。
意气正盛的姚文元,怎么会一下子收声敛息?
哦,这里用得着一句中国谚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反胡风斗争,反到了“英雄”头上来了!
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难忘的一天;他正在机关写批胡风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诉他,说是他的母亲来了。
脏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经带回家洗掉了嘛,母亲来干什么?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楼,只见母亲周修文神色紧张站在大门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边说:“爸爸给抓去了!”
姚文元一听,脸色陡变。略微镇定了一下,他说:“你赶紧走。我下班以后回家。这消息对谁也别讲!”
“你放心。”母亲说,“我怕别人知道,才来机关找你。我怕打电话会被总机听见……”
周修文说罢,急急走了。
下班之后,姚文元悄悄回家了。
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无其事地回到机关宿舍。
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击……
解放之后,姚蓬子仗着有二十三万元(即旧人民币二十三亿元)的资本,仍然开他的作家书屋,当他的老板。
不过,他没有宣铁吾那样的靠山,不能再做纸张投机生意了,收入远远不及纸贩子的年月。
令人头痛的是,作家书屋里的职工成立了工会。工会成了他的对头。
工会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
姚蓬子总是打“太极拳”。实在没招儿了,这才象挤牙膏似的,增加一点工资、福利。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作家书屋并入了全民所有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书屋的职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职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料员——不过她实在干不惯,做了一年就洗手不干了。
姚蓬子在作家书屋关闭之后,干脆,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
他倒有点“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着叛徒历史和奸商劣迹,又是地主、资本家“双料货”,在共产党手下别指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他庆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经济上捞了一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