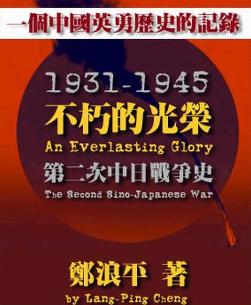战争与回忆-第1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知道身上穿的是什么吗?”
叶市连柯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士兵:“你穿的是新军服吗?”
“是的,将军。”回答得很迅速,年轻的红润的脸流露出警觉的、严肃的神色。“美国制的。好料子,好军服,将军。”
叶甫连柯看了帕格一眼,后者点头表示满意。
“俄国的躯体,”叶甫连柯说,他的话使帕格苦笑了一下。
外边的天色逐渐变亮。一辆斯蒂培克指挥车开了过来,粗大的轮胎掀起阵阵雪花,接着司机敬了个礼。“好吧,我们去看看我的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叶甫连柯边说边把他那棕色的长大衣的领子翻起来,把皮帽扣紧。
维克多。亨利想象不出他们会看到什么,或许是另一个使人意气消沉的莫斯科,只是象伦敦一样被烧焦、被轰炸,疮怿满目。现实使他目瞪口呆。
除了银白色的阻塞气球安详地飘浮在宁静的上空以外,列宁格勒几乎没什么迹象表明它是座有人居住的城市。洁静的、空无人迹的白雪覆盖着一些两旁矗立着庄严古老建筑物的大道。不见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象家乡的星期天早晨一样,但在他的一生中帕格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宁静的安息日。一种令人感到不安的、蓝色的、无边的岑寂笼罩着大地;不是白色而是蓝色,是洁静的白雪从某个角度反射出越来越亮的蓝天。帕格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运河和桥梁;他想象不到如此宏伟的大教堂,或足与爱丽舍田园大街媲美的宽广壮丽的大道,在晶莹的空气中披上银装;或在一条比塞纳河还要雄伟的冰封的河流两旁的花岗岩堤岸上鳞次栉比的宏伟房屋,在指挥车驶上冬宫正面前方那个巨大的广场时,他在一瞥之间完全领略了俄罗斯的雄伟、力量、历史和光荣,就是在凡尔赛宫也看不到如此庄严华丽的景色。帕格记得在描绘那次革命的电影中看到过这个广场,造反的人群和沙皇禁卫军马队发出震耳的吼声。而今,广场上杳无人迹。在这一大片雪地上看不到一条车辙和一点人迹。
汽车停了下来。
“多静啊!”叶甫连柯在十五分钟的沉默之后说了第一句话。
“这是我生平看到过的最美丽的城市,”帕格说。
“他们说巴黎更美。还有华盛顿。”
“没有更美的地方了。”帕格情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莫斯科只是个村庄。”
叶市连柯投以非常奇特的眼色。
“我这句话会得罪人吗?我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了。”
“太不讲外交礼貌了。”叶市连何嚎叫起来。他的嚎叫听起来倒象是一只猫在感到满足时发出的哈噜声。
随着时间的过去,帕格看到很多炮弹造成的损害:断垣残壁、阻塞的街道、到处都是钉上碎木片的窗户。太阳冉冉上升,条条大街都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这座城市苏醒了,尤其是接近德军战线的南部工厂区。在这儿,炮火留下了更严重的创痕;好些街区整个被焚毁了。行人在打扫过的街道上跋涉,偶尔有一辆无轨电车颠簸着驶过,军用卡车和运送兵员的车辆却川流不息。帕格听到远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德军重炮的轰鸣。他看见一些建筑物上刷有这样的标语:市民们!敌人炮击时,街道的这一边更危险。然而,即使在这儿,他的内心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感觉:这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几乎远离战火的和平大城市。这些后来获得的、显得更平凡的印象并没磨灭掉——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磨灭——帕格。亨利那天清早在战时的列宁格勒所见到的鲜明景象:它是一个睡美人,一座蓝色冰雪天地里被邪魔镇住的、属于死亡世界的大都会。
连基洛夫工厂也是一片荒凉气氛。据叶甫连柯说,这儿应该是非常紧张繁忙的。在一幢被炸毁的大楼里,一排排尚未装配好的坦克上满是屋顶坍陷时散落下来的烧焦的碎瓦破屑。几十个戴着披巾的妇女正在耐心地清除碎片。有一个十分繁忙的场所:一个巨型露天卡车场,它广及几个街区,上面盖上了精巧的伪装网,维修工作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工具的叮当声和工人的吆喝声交织成一片,这里是租借物资发挥作用的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一股来自底特律的洪流达到了七千英里之外,德国潜艇无法触及的地方;数不清的磨损得很厉害的美国卡车。叶甫连柯说,这些卡车多半在整个冬季里行驶在那条冰上通道上。现在冰块变软了、铁路也通了,而且那条通道也完了。经过修整后,这些卡车可以调到中部和南部战线,大规模的反击战正在这两条战线上击退德军。叶甫连柯接着领他去看一个机场,部署在机场四周的高射炮群看来是美国海军使用的货色。在弹孔累累的机场上到处是伪装的俄国雅克式战斗机和漆上俄国标志的美国飞蛇式战斗机。
“我儿子驾驶这种飞机,”叶甫连柯边说边拍了拍一架飞蛇式的机罩。“这种飞机挺不错。我们去哈尔科夫时你会碰上他的。”
白昼将尽,他们驱车前往一所医院,去接叶市连柯的儿媳妇。她是一个志愿护士,现在刚下班。汽车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街旁的房屋好象都被一次龙卷风刮去了,只剩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矮小地基,连碎砖破瓦都已荡然无存。这一带的木屋,叶市连柯解释道,全拆掉作为燃料烧了。汽车在一块平坦的荒地上猛然停住,只见那里一排排的墓碑在积雪中露出头来。墓地上到处是人们用随手捡来的瓦砾或碎片——一截管子、一技手杖、一块椅子的板条——或者是用木头或马口铁制成的粗糙的十字架标志。叶甫连打和他的儿媳妇下了车,在十字架丛中搜寻。将军在远处积雪中跪下。
“唉,她都快八十岁了,”汽车驶离公墓时他对帕格说。他脸色安详,双唇痛苦地紧闭成一道横线。“她苦了一辈子,革命前她是一个侍女。她不曾好好上学。不过,她能写诗,很不错的诗。维拉还保存着一些她临死前写的诗。我们现在可以返回营房了,但维拉邀请我们到她住的公寓去。你看怎么样?营房里的伙食好些,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供给士兵。”
“我吃什么都无所谓,”帕格说,被邀请到一个俄国人家里作客倒是件不寻常的事儿。
“那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列宁格勒人在今天是如何生活的。”
维拉对他展颜微笑。尽管牙齿长得不好,她的笑容在顷刻之间使她看起来不那么难看了。双眼蓝中带绿,很漂亮。动人的热情使她容颜生光。她的脸庞以前大概是相当丰满的。松弛的皮肤有了皱纹,鼻子显得很尖,两个眼窝象是深暗的洞穴。
他们在一处很少受到破坏的街坊走进一座阴暗的门道,一阵阻塞的便池和烧油锅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们在黑暗中走上四段楼梯。接着听到开锁的声音。维拉点亮了一盏油灯,在稍带绿色的灯光里,帕格看到这间斗室里塞满了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瓷砖炉,炉子周围堆放着碎木片,马口铁烟筒歪歪斜斜地通向一个用木板堵住的窗户。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因为外面太阳刚才下山。维拉点燃了炉火,敲碎了水桶里表面那层薄冰,然后把水倒入水壶。将军从他带上楼来的帆布袋中取出一瓶伏特加,放在桌上。尽管穿上厚实的内衣和笨重的皮靴、手套和一件毛线衫,帕格还是冻僵了。这时他自然乐于和将军一起喝上几杯。
叶市连柯指了一下他坐着的那张床说:“她就死在这儿,还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维拉没办法弄到一口棺材。没有棺材。没有木料。维拉不愿把她象一条狗那样埋在土里。天气很冷,零下好些度,因此卫生倒不成问题。可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骇人听闻。但维拉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象安安稳稳地睡着了似的。首先死去的当然是老年人,他们没耐力。”
房间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维拉在炉子上煎薄饼,她脱掉了披巾和皮上衣,露出一件穿破了的毛线衫,裙子下面是厚厚的护腿和皮靴。“这儿的人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吃,”她平静地说。“皮带、糊墙纸上的胶水。甚至狗和猫,耗子和麻雀。我才不吃呐,我吃不来那些,但我听说过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我们听到了一些吓人的事情。”她指着炉子上开始瞠噬发响的油煎薄饼。“我用锯木屑和凡士林做过这种薄饼。可怕得很,吃了难过死了,不过是为了塞满肚子。那时候有少量的配给面包,我全给奶奶吃了。但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再吃了。她没有感觉了。”
“把棺材的事情告诉他,”叶甫连柯说。
“有一个诗人住在楼下,”维拉边说边翻动在煎锅里劈劈啪啪响。的薄饼。“利茹柯夫在列宁格勒很有点名气,他拆掉了他的书桌,给奶奶做了一口棺材。他现在还没有书桌。”
一还有那大扫除的事情,“将军又说。
他的儿媳妇一听,就没好气地顶撞了一句:“亨利上校可不想听这些伤心事儿。”
帕格吞吞吐吐地说:“如果说起来使你伤心,那就算了。不过我倒是很想听的。”
“那好,以后再看吧。现在吃饭了。”
她开始在桌子上摆餐具。叶市连柯从墙上取下一张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的照片。“这就是我的儿子。”
灯光下他看见一张端正的斯拉夫面孔:卷头发,宽额角,高颧骨,天真聪颖的神态。帕格说:“漂亮。”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
“我有过。他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了。”
叶甫连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用他那只好手紧紧地抓住帕格的肩膀。维拉从帆布袋里取出一瓶红酒放到桌上。叶甫连柯拔去瓶塞。“他的名字?”
“华伦。”
将军站起来,倒满三杯酒。帕格也站了起来。“华伦。维克多维奇。亨利,”叶甫连柯说,炉火使这个灯光照射下的邋遢的小室变得闷热了。帕格喝下那杯略带酸味的淡酒时,感觉到——这是第一次——华伦之死给他带来了一种不纯粹是极度痛苦的滋味。不管为时多么短暂,华伦之死弥合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叶甫连柯放下他的宝杯。“我们知道这次中途岛战役。它是美国海军一次重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的形势。”
帕格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除了薄饼之外还有香肠和来自将军的帆布袋里的美国罐头水果色拉。他们很快就饮完了一瓶酒,接着又开了第二瓶。维拉开始谈到被围后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她说,发生在去年春天三月下旬解冻开始时。尸体陆陆续续在各处出现,他们都是倒在街头就死去的人,几个月来没掩埋的冻僵了的尸体。垃圾、碎砖破瓦以及各种残骸和成千上万的尸体一起出现,造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到处是一股使人作呕的恶臭,瘟疫严重地威胁着人们。但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把人民组织起来,一次大规模的清洁运动拯救了这座城市。尸体被投入巨大的集体墓穴,其中有些人查明了身份,但许多人都无法查明。
“你知道,全家人都饿死的有的是,”维拉说。“或者只剩下一个人,不是病倒了就是失去了感觉。如果有谁不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唉,一个人快要死了,你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变得麻木,无所感觉。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医院,或让他们躺在床上,设法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