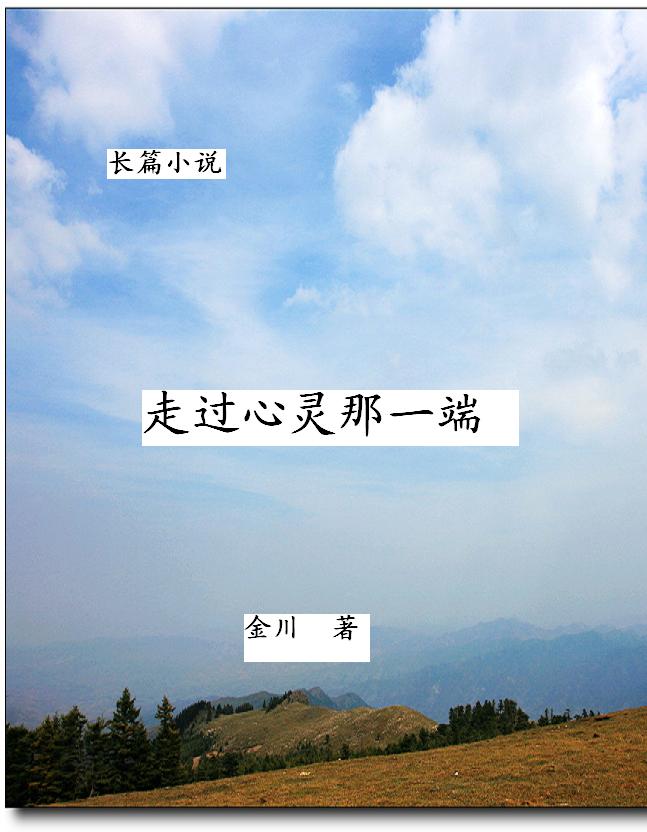走过西藏-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着卓玛拉顶峰在望,索性走得更慢了。一群老老少少转经者二十多人从后面赶上来。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妇女盯住我打量好半天,目光里透着友善。我也冲她笑笑,于是她便问我从哪里来。我乐意攀谈,提问和回答。她就说她叫冬米。冬米,冬天的冬,大米的米,她补充说,她在改则县气象站工作,家住县医院,让我们路过改则时一定去找她。这群人都是改则县上的,乘东风大篷车来的,已经来了六天,转了三圈了。不打算久住,再转两圈就回去。
因为今年马年,来转山的特别多。据说阿里有关部门已通知干部不要参加转山,但差不多所有人都来过了。有些单位派车是以“春游”的名义。我觉得来转山没什么不好,如同参加民间聚会和节日,至少没任何坏处。凡转山者都怀有虔诚善良之愿,是一次纯净的精神之旅。
但是也有例外,就在卓玛拉山顶小小的碧绿湖旁,前几天有一康巴姑娘被害,各种首饰被洗劫一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至圣神山杀人越货罪孽将倍加深重,应永世沦入地狱不得进入轮回的。这座湖就是传说中的湿婆之妻乌玛女神的沐浴湖。
太阳升起时我走到卓玛拉山顶。同行的人们已久候在此。山顶冰雪覆盖,寒风料峭。红红绿绿的经幡交错垂挂如网。在同伴们的高声敦促下,我从一石缝中爬钻过去——早有人等此镜头。据说有罪之人是钻不过去的。
山顶之湖小如镜面,湖畔是斑驳的雪。太阳明亮耀眼地照在上方的山上,山窝的湖则在阴影中。受不住山顶的凛冽寒气,就急着下山。上山路为缓坡,下山却急陡,狭路险且不说,融雪冻成冰,一步一滑。只好临时结伴,手拉手在峭崖石区一步步寻找路眼。毕竟是下山,心里轻松多了。不止我一人,所有人都轻松。该死的小韩和次丹多吉,事后才揭发了自己:他们开始转山时内心虔诚而紧张,按照某种迷信,他们居然回避与女人同行。翻过了卓玛拉,小韩才敢于接近我,半拉扯半搀扶地走过最难走的路段。
此刻我们已转到神山东侧,风景大变,远不及昨日,所见之山为风化严重的碎石山,整座山仿佛一触即溃。也有许多传说,是许多神的殿堂。按照我的新观点,一概不去打听:多少年来我也没搞清西藏土著神灵的谱系与归属。不去打听,免得添乱,心里也在反驳说,看这寸草不生的乱石山,哪里像神仙住的圣地!
神山东侧的宽谷地带仍有河水流淌,有草泽,偶有帐篷羊群。在神山脚下吃草的牛羊有福了!多年前此地肯定发生过泥石流,硕大石块密布谷底,已被流水磨去棱角,我们就在圆石上跳跃前进。在一处草坪上,又烧茶吃饭,欢天喜地,像过林卡,野餐。这一侧所见神山之巅则如圆的馒头。主体部分则被一旁世俗之山遮挡。小韩殷勤地与我结伴同行,然后海阔天空乱吹一番。在明净的自然之中心境如此姣好,真是罕见。人际关系也清纯透明如水晶,直到现在我仍惊异于那时的感觉,就总想着此生再没有比转山的那两天更愉悦的心情了吧。
总是激动地诉说的次丹多吉一路同我交谈,文学,艺术,他的民族文化习俗,他所能想起的众多的研究课题,他的焦虑——“我看到土林的流痕,就觉得它们是我祖先的眼泪;我看到山野荒风中的断壁残垣,就觉得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眼泪……”他比我对于职业的选择更盲目,简直就无所适从:他感兴趣并确有相应小才气的领域太多太广。在转神山的这一天他说:“我觉得我的躯体属于这个世界,而我的灵魂,则属于另一世界。”
在一处山崖下,土红色的河水汹涌而下。次丹多吉就说,神山另一侧的清溪是神水,这一侧的浊流是药水,可治多种疾病,因为是冲刷着神山的红石崖而来。他就用这冰冷的水洗了头。我则洗了手脚。于是我们就远远落伍了。
太阳还高,时间还早,转过这个山弯,就是几公里长的汽车道可直达塔尔钦了。次丹多吉眼睛一亮:“好像是我们的车在等我们吧!”随即他又叫了一声:“看,(格勒)老师来接我们啦!”
我们立即加快了步伐,已能辨清格勒快步迎来的身影。一向对自己的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次丹多吉,这时忍不住就语无伦次起来:“我觉得,我们老师太伟大啦……看着他的动作,听着他说话,都让人觉得……多亲切,多好!”
格勒满脸是笑地迎上来。我像小女孩似地大叫大嚷:“老师!快亲我们一下!”
身穿天蓝色鸭绒眼的格勒张开双臂,一左一右把我们揽进怀里,再一左一右贴了脸——昨天早晨才分手,怎么就有隔世之感哪!
格勒说,本意是想车接一段,但前面那几位都说不能功亏一篑,余下的路坚持步行,谁也没上车。当然,我和次丹多吉也不坐。就迎着夕阳走回去。
就向格勒谈了这两天的主要感受和重大决定。此前,格勒曾勉励我说:“你很勤奋,可以成为一个好学者。”——对不起,嗨,我说,我不打算做学问了,这是神山给予的启示。
另外,我又说,转山前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以往极不善走的我,一圈下来竟技状态尤佳。我觉得,这是神山给予的加持。
当然,神山的馈赠远不止这些。
格勒耐心地微笑。他心里一定在想,喜欢激动、夸张和多变是文学人的毛病。
文学之路在脚下继续延伸,然而再次迈出的脚步是新鲜的。内容已有所更换,看待世界的视角也有所调整。
这个世界不喜欢愁眉苦脸,不耐烦弱者,那么我从此不再去展示创伤,侈言苦难。
这个世界有多种境界,且让我一如既往地远物质、重精神,避喧嚣、多沉思,终生面向优良境界,并为世界作这一方面的代言人。
这个世界引我在它的极顶处盘桓,让我穿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翻越横断山,走向冈底斯、喜马拉雅山,用心良苦。尽管它不喜欢傲慢骄狂,仍然默许了谦恭表象之下的卓然不群、孤芳自赏。
我们地球被佛家看作三千大世界中一小世界。三维空间狭窄。人生苦海无边。令佛心格外垂悯。
这个小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
亲爱的山,亲爱的、亲爱的——世界!
在苏黎世,一位高个子瑞士朋友送我一本英文版的有关冈底斯的名为《神山》的画册。我以有限的英文能力从中随意辨识并翻译了这样的一节——……凯拉斯在寒冷的月光下闪烁,永恒而难以理喻。香客们误以为它仅为朝圣所设,而作为信仰的凯拉斯是一面镜子:雄伟壮丽并反映着投射其上的神性灵光。它本身不具备更多,除了石头和冰雪。但通过对它的凝视,它给予的一瞥成为无限。
第五章 荒原小城狮泉河镇
——阿里及其三图名称由来传说——从噶尔昆沙到狮泉河,阿里首府的变迁与沿革——最偏远的又是最尖端的:阿里的太阳房和光电站——四十年前的一桩往事——狮泉河镇经商者——并非故乡风景中生长出来的狮镇文化,来不及从容不迫——为万里之外的儿子做生日——一切都很值得——
阿里地区现有总土地面积三十万五千平方公里,总人口六万零五百人,差不多平均每五平方公里为一人。下设普兰、扎达、日土、噶尔、改则、革吉、措勤七县。其中后三县为纯牧业县,在自然地理上属藏北高原。据阿里的历史概念,则不含藏北高原,仅指被称之为“三围”或“三环”的普兰、扎达、日土三地,分别为雪山环绕、岩石环绕和湖泊环绕之地。据其历史地理,先归象雄,再归吐蕃,元朝时划归纳里速古鲁孙宣慰司,明朝则归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古代阿里高原曾沿用过的名称,最早可查的为大羊同和小羊同(象雄转音);到吉德尼玛衮开创古格时代后,又称“领域三部”(纳里速古鲁孙之意译);而在民间传说中,则认为在甘丹才旺之后,才明确地出现“阿里三围”之称。这一传说集中了阿里及三围各名称来历的民间说法。
如前所述,拉达克王朝与古格王朝的创立者本是亲兄弟。但三弟德祖衮选择了北方玛隅建起拉达克王室后,由于地理遥远与两位哥哥交往渐疏,终至后代反目成仇,屡动干戈。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灭古格后,举兵东进,侵犯后藏,达赖政权不得不出兵反击。
此时的甘丹才旺身为清朝敕封的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蒙古汗王的兄弟,也是出家僧人。应召出山时还了俗,亲率三千名蒙藏骑兵西征。由于他的军功,他成为阿里人有口皆碑的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的传说堪与格萨尔王相媲美。由于阿里近代史上没有更值得一说的业绩,阿里人至今仍津津乐道。
甘丹才旺骁勇异常,拉达克人闻风丧胆,一将落荒逃回列城,正在召集残部时,甘丹才旺从噶尔的扎西岗一箭射中了该将的头盔。有人问你是神还是人?甘丹才旺说,我是人,但衣冠穿戴与众不同。于是拉达克人摹仿甘丹才旺的穿戴据说直到现在。
心服口服的拉达克人送来许多杏干,甘丹才旺又转呈给藏政府。拉萨人不知来历,想当然地以为阿里所产,取地名阿里是“甜山”的意思。
甘丹才旺驱逐拉达克主要赖于三场战役。在向藏政府的战况报告中,甘丹才旺描述了三战役的情况:第一次战役在雪山环绕的普兰,歼敌像“拔一根毛一样”容易——普兰,即一根毛之意;第二次战役在岩石山环绕的扎达(扎布让),歼敌则像“拔一根草一样”容易——扎布让,一根草;第三次战役在湖水环绕的日土进行,歼敌较为困难,像“啃骨头”一样——日土,啃骨头。
——这是有关“阿里三围”之名由来的又一种解释。
阿里百姓与屡屡进犯的拉达克人不共戴天,杀死拉达克俘虏无数。在普兰多油乡,建有三座佛塔,名“崩莫切”,意指塔下埋十万人,为死者超度。虽已残破但该塔犹存。
甘丹才旺此前为僧人,率兵征战的需要才还了俗。虽然战功显赫,终是杀人如麻。于是战后在普兰县城建一贤柏林寺以赎罪。
光复阿里之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立了正规的行政建制,由甘丹才旺选择了今噶尔县的噶尔昆沙和噶尔雅沙作为首府(冬、夏季驻地)。藏地称其为“堆噶尔本”,后改称“噶大克”。噶尔本下设四宗六本。噶尔本官员由拉萨的噶厦政府直接派出。由于阿里地处边境,噶尔本官员的品第较高为四品官,每三年轮换一次。甘丹才旺是第一任噶尔本(专员)。按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噶尔本也照例是一僧一俗。僧官名次在先但不主事;俗官名列其后但掌握实权。这些官员品第虽高,来阿里任职也只好住帐篷。各宗官员及头人时常来拜访噶尔本,就称阿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乌固”,乌,帐篷;固,尊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噶尔本留在噶尔昆沙的官邸还只是一排夯土的破旧房子。
当我沿着象雄——古格——近古阿里的脉络检索一番,自以为已大体明晰并尝试了粗线勾勒之后,不意近日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发现一明代档案原件,为明洪武六年的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朱元璋敕封溯思公失监为俄力思(阿里)军民元帅的圣